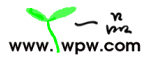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杜维明 衣俊卿
xinmaopai006 发表于 2009/09/06 00:11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衣俊卿(以下简称衣):很高兴有机会当面向杜先生求教。杜先生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涉猎颇广,例如对儒学,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对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的发掘,对韦伯、帕森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启蒙和现代性争论的分析,等等。今天我想就启蒙的反思问题向杜先生求教,在这方面您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儒家伦理与全球社群等众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而且启蒙和现代性也的确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焦点性问题。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好的。
衣:我希望今天的讨论撇开拒斥还是捍卫现代性这种笼统的非此即彼的宏大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您的基本思路的:一方面您特别关注启蒙和现代性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另一方面您对自由、理性等启蒙的核心价值一直持肯定态度。您强调:“现在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些价值是不是应该扩大延伸,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而是面对人类所碰到的困境,这些价值全都加在一起,是不是足够?”
杜:是的。
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不是简单拒斥和抛弃的问题,而是对它的完善和继续推进、深化,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如何调动各种精神资源。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我一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各种理论比较熟悉。我并非对现代性的后果视而不见, 但是,对于启蒙和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我是充分肯定的,特别是基于中国的特殊语境,我的观点可能更彻底一些。今天,我想循着您的思想谈谈如何具体地动员儒家的资源。我建议,我们的对话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如何对各种精神资源作具体的分析,从而更加扎实地而不是笼统地进行启蒙的反思;其次,回顾东亚国家动员儒家资源的成功经验,探讨儒家伦理对于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而分析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真实的相关性问题;最后回到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看看儒家伦理的弘扬和反思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考察一下这种关联是一般性的关联还是实质性的关联。不知道这三个问题是否合适?
杜:可以。但是我不一定准备得非常充分。
衣:其实,我选择的这三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困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对话事实上是向您求教。我向来对儒家文化批评很多,但我所作的不是无条件的一般性的批评,而是具有深层语境的批评。
一、如何对启蒙的精神资源进行扎实的而不是笼统的反思
衣: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更加扎实而不是笼统地进行启蒙的反思。哈贝马斯曾经在一个对话中谈到,现代性不是一个总体性的、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不是通过一次讨论就可以决定要还是不要的东西。现在很多对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是停留于一个总体的取舍问题,进行一般性的描述,而没有深入到根基性的东西。今天我们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要集中讨论您所提出的动员各种精神资源来超越启蒙心态、构建全球社群的问题,还要特别对不同的精神资源作具体的分析,特别要考虑这种启蒙反思方案的具体可操作性问题。
杜先生深入地揭示了启蒙的本质特征,反思了启蒙的自身缺陷和消极后果,如理性化、世俗化、科学化、技术化、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社群瓦解直到最极端的雅格宾专政和“奥斯维新”等。这些批判在此不用展开,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很关注也很熟悉。但是我非常关注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您对启蒙核心价值的肯定。比如说,您在和黄万盛教授的对话中说道:“从儒家的立场看,自由、理性、法治、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价值,不管你的视野多么狭隘、抗拒西方的心态是多么强烈,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价值。”[1](P65)您接着说:“个人主义、突出个人和启蒙开辟出来的几个利益领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方社会,或者说任何一个社会要蓬勃发展,这些价值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1](P65)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您认为启蒙的核心价值不是如何取消而是如何扩大的问题。您过去经常谈论启蒙的三种精神资源:第一个是启蒙的源头,也就是“两希”文化;第二个是东亚、中国的资源;第三个资源是美洲等一些本土资源。后来您又提到女权主义的资源。这些观点,我总体上赞同,而且我正在做一个关于现代性维度的课题。我现在考虑的是,我们只是把这些精神资源罗列出来而不作具体的分析还是不够。此外,按照您的逻辑,我认为还有一些资源需要列入,如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等。
但是,一旦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这些资源和启蒙有着不同的关联,“两希”文化和女权主义是启蒙运动内在的资源,而东方和美洲资源是启蒙运动外在的资源。这种区分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视角。如果启蒙只有外在资源而没有内在资源,我们很容易判它死刑,并用其他的东西取代它。如果它有内在资源,那么对它的判断将很不一样。因此,这种内在资源和外在资源的区分应该是根本性的。
杜: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中肯。我现在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提出那些观点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距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首先,启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刚才讲,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个历史文化现象,不是理念的问题。一方面,启蒙确实是一个文化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伏尔泰、莱布尼兹、卢梭、狄德罗,还有“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都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回到源头,启蒙的出现是反对基督教神学,特别是神学代表的政治权威。当时最重要的参照就是中国社会,这和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儒教经典有关。同时西方社会了解到,中国明代社会不仅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变化很大,而且18世纪以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当时的学者经常谈所谓“中国的风尚”,当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的,但是还有更为深层的反思,当时伏尔泰和卢梭的辩论,伏尔泰突出文化的重要性,卢梭要回到自然,他们对文化的观点不同,所以对儒家的了解有所不同。西方社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没有西方的上帝而社会秩序达到那样一个程度,例如商业资本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基本稳定等。中国的官僚制度直接影响了英国的文官制,可以说非常先进。因此说,启蒙的产生,儒家思想可以算做一个因素。现在很多人想了解这一点,作了很多研究,甚至编了百科全书。好像是尼采有一个说法——当然是一句玩笑话,说康德是“柯尼斯堡来的伟大的中国人”。康德的思维和基督教的思想方式确实有所不同。虽然他讲上帝存在、灵魂永恒,但是,他的理性的观念,如果从基督教的传统看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基督教的传统是靠信仰得救。康德的理性的观念在很多地方可以说和中国的思路,特别是和儒家的思路有相契合的地方。牟宗三先生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专门讨论康德和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
衣:您的意思是说,儒学和启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资源的关系,而不是外在资源的关系。
杜:有这样的可能性。是不是内在很难说,但是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启蒙的内部资源也很复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有很大的不同。哈贝马斯说,启蒙的大的计划(project)还没有完成。德里达则要求从启蒙跳出来,他后来一直讲逻格斯中心主义(logs-centrism),不仅是启蒙,他还要反思整个西方文明,这很像海德格尔要回到苏格拉底甚至苏格拉底之前,也就是回到存有(being)的声音,这个声音我们已经听不到了。
启蒙也有阴暗面,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说,只要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明启蒙的黑暗面,这个词就是“集中营”。
西方的启蒙这么复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文化多样主义等对启蒙的批判,都是西方文化的内部问题。我们现在考虑的很多问题,要么来自西方的启蒙和现代性,和“西化”连在一起,要么就来自对启蒙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马”也都是在这个大传统里发展的。所以我说,启蒙内部的资源非常丰富, 而且多元多样。
去年,美国的人文学会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他们认为儒家是一个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它没有上帝的观念——虽然利玛窦认为有。我觉得有些不安,启蒙所代表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是一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它的问题不在于理性化,理性化本身是健康的,它的问题是工具理性,它的工具理性特别突出。比如说,在古希腊那里,“知识是智慧”,在培根那里,“知识是力量”,力量是理解, 甚至征服自然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浮士德的精神。它追求真理、价值是不顾后果的,甚至可以出卖灵魂。在这里,儒家讲的修身不起作用,唯一重要的是人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客观的集合体,它是“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是人赋予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不仅很紧张,甚至可能到了破裂的程度。
我特别提到“启蒙的心态”。我想解决的问题是:启蒙的理性落实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脉络中间起的是什么作用?我认为,科学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五四运动的开始阶段讲自由和人权,后来讲科学和民主。讲科学和民主的时候已经和原来接受西方文化时的意愿有所不同。就是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导致了工具性过强。科学当然可以使我们强盛,民主可以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学不是追求真理,它的动机是发展;民主也不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而是动员社会来面对外界的挑战。“启蒙的心态”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影响非常大。
衣:非常感谢您所作的详细解释,包括对儒学可能已经内在于启蒙运动中的解释。您还提到神圣维度的问题,此外,还有审美现代性和浪漫主义的问题。
我想朝另一个方向思考。我不喜欢“多元的现代性”这个提法,如果说“现代性中的多元性”还可以考虑。我想说的是,启蒙运动中有这么多的资源, 今天对启蒙的反思实际上是启蒙自身的事情,不是启蒙之外的事情,不是在启蒙之外对启蒙的批判。甚至我们东方人也是在启蒙自身内思考问题。我的结论是,启蒙也好,现代性也好,不是一个完成的和封闭的东西,它本身就有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修复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我从来不认为“后现代”形成了对现代性的断裂,它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延续,自我修复的延续。比如,吉登斯谈到的现代性具有的反思性。这样看,对现代性的担忧就不应该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
杜:我们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分歧。你赞成现代性中的复杂性,有各种不同的资源,而不能接受“多元现代性”。这和我与埃森斯塔 (S. N. Eisenstadt)的激烈辩论相似。最近,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机关报《代达罗斯》(Daedalus)出了一个专号(它经过很多年的筹划,我也参加了)。西方比较文化学界的埃森斯塔和我合作以“多元现代性”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埃森斯塔一直要强调“现代性中的多元”。我们的研究结束后,他提出以“现代性中的多元性”(many facities of mordenity)发表,我认为应该是“多元现代性”(multipal mordenities)。当时的讨论很激烈。有一位瑞士的学者赞成我的观点。他有两个想法:保守的想法是西方的现代性还要发展,因为它有着充分的内在资源。另一个比较开放的想法是,东亚的现代性提供了西方之外的现代性类型。东亚的现代性是否来自于西方传统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我问过丹尼尔·贝尔,接不接受西方之外的现代性。他说,有太多西方之外的现代性,但是每一个都是失败的。他当时有一个看法——后来亨廷顿讲文明冲突时也是同样的看法,表面上我们可以想象不同的现代性,但是这些现代性是站不住的。
“多元现代性”和“现代性中的多元性”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启蒙所发展的现代性内容非常复杂,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还有浪漫主义对它的批评。因为现代性的多元多样,它有很多的张力,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现在很难跳出来。我的观点是,在西方之外,比如中国,对启蒙的信念和要发展启蒙的愿望比西方要大。所以说,启蒙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势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启蒙蜕变出来的。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受惠者,有人说,也都是受害者。现在往前看,最全面的启蒙所代表的精神对人类的发展是否是足够的精神资源。如果说,启蒙的资源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足够了,那么自然的问题和宗教的问题怎么样纳入它的传统。
衣:我认为,现代性最核心的特征还是在以理性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发达国家率先生成的。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都是现代性的他者,所以才有“后发现代化”的问题和“启蒙心态”的问题。这些他者对于修补现代性如果有作用的话,首先要有具体的机制。您强调东方的宗教的和非宗教的精神资源, 以及美洲的本土资源等对于反思启蒙的意义,是说这些资源在这些本土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超越启蒙心态、抑制和修补启蒙的价值,还是说这些资源对于全球范围内,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克服启蒙的危机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些资源通过何种方式或机制才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启蒙理性的进一步深化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您的观点和哈贝马斯恰恰是可以互补的。在当今世界中,启蒙之外的这些本土资源无论如何重要,在整个世界格局中还是处于边缘位置。我们需要某种机制让它们能够进入对话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只有在这些社会自身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才有可能起到缓解和组织作用,而不会对整个世界的主流话语产生作用。您对哈贝马斯的某些批评,我是同意的。但是他的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恰恰可以作为机制引入到您的精神资源说中来。
杜: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工作可能不是修补现代性。
衣:是在启蒙之外再发展其他的现代性吗?
杜:也不那么简单。我考虑的是:可不可能存在启蒙的他者对启蒙——不是修补,因为修补已经来不及了,而是共创一个新的人文世界。这个新的人文世界在现阶段,启蒙是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它不是启蒙的自我修补和内在转化,这个内在转化是非常艰难的,只有通过他者的参照才行。
我觉得,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多少有一定的说服力。所有他者面对启蒙,其声音都很微弱。但是我们要了解启蒙之内的一些变化,以前没有想到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很多一流学者对21世纪作了很多预见,现在回头看,他们有很多没有预见到的地方,例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女性主义在现在影响这么大;还有就是没有想到生态、环保问题这么严重。
事实上,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是启蒙反思的最重要的两个思潮。女性主义大大地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家庭、两性的关系和权力结构等,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核心价值方面。我现在问各位,在以下价值对中如果你只能选择一种——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你会怎样选择,你选择哪个就举手。这些价值是:自由和正义(与会听众选择正义的占大多数——编者注,下同),理性和同情(选择同情的略多一些),法治(legality)和礼让(civility)(选择法治的占多数),权利和责任(选择责任占多数),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选择社会和谐略多)。你们所作的选择中除了对法治和礼让这一项外,其他的都是倾向于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对启蒙的这些质疑和儒家的基本价值合拍。对于儒家,正义比自由更重要。从康德哲学讲,道德推理当然要靠理性。休谟和亚当·斯密提出了道德情感(moral senses)问题。在康德之后,这些苏格兰的启蒙变得“不够严格”了。现在,人们对康德最大的不满在于他对情的问题和对人性的问题的理解不符合人们一般的常理。权利对于西方太重要了,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有了权利才有责任。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责任发展权利呢?我指的是,越是拥有权力、资源、信息的人越应对社会作出贡献。中国的这次赈灾活动就是例子,越有钱的人捐献的越多,人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尽的责任。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愿不愿捐献是个人权利。和谐社会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和谐是每个人能够有尊严、能够存在的先决条件。这些价值是否能从启蒙理性中推出来,是很成问题的。
衣:我同意您以上所说。但是,是否可以按另外的逻辑来解读。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还是从西方原有的启蒙中开出来的,而不是西方之外的东西。我认为,不能因为女权主义和儒家价值有些相似之处就说它是我们的资源。也没有证据证明西方的女权主义是受了儒家伦理的影响,相反,它完全是西方文化内部发展出来的。我认为,女权主义是微观政治的产物。就像福柯说的那样,西方社会的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宏观控制的社会,所以边缘群体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这才是女权主义产生的背景。因此,我还是认为,启蒙有着丰富的内在资源使得它能够发展出自我修正的资源。基本上说,西方的女权主义在中国影响很小,因此说,它和中国的文化语境没有什么关联。我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的女权主义所讨论的那些问题。
杜:中国的女权运动有它自身的特色。事实上,各个国家的女权主义都是不同的。在中国,女性和男性之间还有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说退休年龄和薪金上的不平等。我认为,在中国,女性的觉醒会成为一个潮流。生态、环保问题起源于1968年,启蒙时代的人是很难想象到环境问题的,甚至黑格尔这样的“全球性的思想家”也是非常西方中心论的。因此,目前的文化多样化主义也不可能是启蒙内部的资源。这些都是新的东西,也许只可以说启蒙的复杂的面向可以把它们包容进去。
衣:我认为,女权主义的前提是启蒙核心精神的充分发展,如果没有个性解放和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女权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在权利意识的基础上女权主义的反思才有可能。中国没有这样的权利意识,因此西方那种女权主义不能自发地产生。因此,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启蒙的核心价值。西方的女权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中国的女权主义还是处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自发的状态中。中国是否存在女权主义不能仅仅通过观察女权主义和儒家价值之间的相似性而作出判断。
杜:我刚才说的问题不是说西方女权主义是受到了儒家伦理的影响才产生的,只是想说明儒家伦理和女权主义是合拍的。
核心的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之中是否缺少自觉的、内在的、反思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你的论点我绝对赞成,但是如果有,我们还可以商讨。这样说吧,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对个性的理解,但是并不表明一种文化突出有个性,另一种文化只有集体性。
儒家到底有没有自己发展出来的个人的尊严和自觉的反思?雅斯贝尔斯在思考轴心文明的时候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世界几个不同文化发生超越性的突破(transendental break through)。犹太教出现了一元的上帝,希腊出现了逻各斯,印度出现了梵天,佛教出现了“空”,儒家出现了“天”。但是儒家的突破最弱,因为它和早期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创发性不够。后来有位以色列学者对此非常不满,他说,如果所谓突破是突出“两希”文明逻各斯和上帝,这对其他文明是不公平的。他提出“第二序的反思”,也就是对思想的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数学,比如说几何学。从“第二序的反思”来看,儒家的出现是对人如何做人(how to be human)的思考。这个反思的思想脉络相当复杂。“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就建立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如果学习不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人格,而是为了父母、社会、国家、身外的外在价值学习,这不是儒家的观点。修身哲学本身就是“第二序的反思”。我们以前把修身哲学当做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儒家的修身不是简单的个人的问题。儒家对思的考虑就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智慧问题。在希腊哲学中,如果生活没有进行反思,不经过考验,那么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衣:我赞成您对中国哲学考虑人如何做人的分析。您可以把儒家的修身哲学和西方的反思哲学类比。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西方的启蒙是一个普遍的教育,因此这种反思性和个性是普遍的生存状态,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是非常贴近自然的,是自在的经验的生存方式。传统中国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人间的等级制,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教育,才有闲暇考虑如何做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大学规模太大,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它只考虑很少一部分人的教育。我希望批评现代性的人们到占中国人口 70%的农村去看一下,看一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少数精英具有反思精神和个性,民众则是麻木的和非个性的,绝大多数人停留在仅仅是活着的水平上。当然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存在着“现代城市的乡村心灵”的现象。我认为,儒家和道家之所以能够互补地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在于它们从来不作超越的反思,而是把天然的君臣、父子、夫妇的自然关系和血缘关系放大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关系。大多数人都是靠这种血缘伦理生存的,只有少数人在搞心性修养。这和启蒙中的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儒家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拉开距离从远处看很漂亮,但是走近看时远远不是那么回儿事。还有一个“文化虚伪性”的问题,即便少数精英也常常没有践行他们所宣扬的东西。
杜:我看过五四以来很多对儒家的批评,包括柏杨的批评、李敖的批评。确实有你刚才讲的现象,虚伪的、堕落的,鲁迅谈得更露骨。
我先说一下对儒家阴暗面的理解,不然容易把儒家美化。我认为,现实地考虑,一个充分、彻底政治化的儒家社会远远要比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更残忍,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更厉害。法家社会只是在行为上规范人,但是充分政治化的儒家社会对人的思想压抑、个性压抑更为严重。我赞成你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心灵的积习(habits of heart),中国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走后门、裙带关系、不透明、官商勾结等与儒家有很大的关系。韩国、日本、越南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儒家维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长期存在,它也一定有一些健康的方面。健康的东西和不健康的东西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和启蒙发展的复杂性相似。
确实,人格的充分发展,不要说成为圣贤,就是成为君子都是非常难的。但这是充分的发展,还有一种最低的要求。事实上,儒家没有出现希腊哲学代表的精英主义。希腊哲学只有几个哲学家。甚至在现代西方,像你这样注重日常生活的哲学家很少,作为哲学家关心的只应该是思辨,比如说对罗尔斯最复杂的论证只有精英才能掌握。基督教通过信仰得救,只有先知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一般人听不到,要通过先知的教导才行。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如果你讲的东西一般人听不懂,那你就出了问题,不是听者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人和一般人的人性是相同的,所以,儒家没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结构。汤一介先生认为修身是少数人的问题,绝大多数人为生活忙碌不能修身。我说这完全不是儒家。一个社会如果是损己损人的人多,这个社会就不和谐;推己及人的人多,这个社会就和谐。如果有一大批人损人而不利己,那这个社会就愚昧;有一大批人损人利己,这个社会就是自私自利的;如果有很多人利己而不损人,所谓“经济人”,这个社会还可以;最好的社会是推己及人。这样一个社会和修身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社会没有在日常生活之外建构或者想象一个精神世界,没有未来的天国,没有彼岸。所以说,儒家对传统中国和基督教对传统西方的影响之间要有些分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