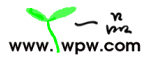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
xinmaopai006 发表于 2009/09/06 00:13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衣俊卿
二、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的真实关系
衣:我们已经把各自的思想谈得比较清楚了,我想,对各种精神资源同启蒙反思的多种可能的关联还是应当作更多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涉及儒家伦理同启蒙的关系,我们可以转到具体的例子上,也就是“东亚对现代性的挑战”这一点的分析上。《新加坡的挑战》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果我们想用东亚现代化的成功例子来说明儒家文化能够支撑现代化,那就需要弄清儒家在东亚现代化中起的作用。我认为,不能仅仅从结果上看,东亚完成了现代化,就说儒家对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另外,我们还要问,东亚的例子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我把您的主要观点归纳为:(1)资本主义和实业精神在东亚的蓬勃发展否定了韦伯的观点,韦伯断定“儒学伦理抑制了一种实业精神的发展 ”[2](P87);(2)有些学者认为,“正是那种在东亚文化的范围中经历过如此彻底的批判的儒家伦理,作为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以及由此类推—— 在新加坡的变化的重要动力,现在正在重新出现”[2](P118);(3)“我一想到儒学和现代化的精神可能很有必要联系就感到兴奋……我极希望见到对于这样一种联系的扎扎实实的实验性研究。”[2](P88)我想问,您有没有作过这种“扎扎实实的实验性研究”。
这里首先的问题是,东亚现代化的蓬勃发展的事实是否就证明儒家伦理就是这种现代化的动力。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儒家伦理作为动力支撑了现代化,没有儒家就没有东亚的现代化,也就是儒家和东亚现代化之间是积极的关系;另一种可能是,儒家文化没有能够完全抑制现代化,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动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关联。进一步地,我想问,儒家伦理究竟是促进了东亚的现代化,还是排除了儒家的阻碍东亚才实现了现代化?东亚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知识背景究竟是儒家的还是西方的?如果儒家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那么东亚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再具体一些,如果儒家伦理是东亚现代化的动力,东亚的现代化有没有构成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精神,或者说是修补了启蒙的缺陷从而确定了更加完善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化是证明了您说的启蒙的核心价值,还是确立了不同的核心价值?还有,东亚的现代化吸收了儒家资源是否说明它的现代化就比西方优越?如果是,其优越性的标志在哪儿?我看到的恰恰是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是全球性的,但是在东亚的现代化中要比西方严重。这些现象是儒家文化没有修补好西方现代性,还是儒家文化自身造成的?特别是东亚的家族企业,当无法支撑下去的时候,又要转向法人治理结构,这说明什么问题?最后,假如说,儒家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它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适用?也就是说,儒家是否具有普世性?您说要作“扎扎实实的实验性研究”,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论想象。我的想法是,新加坡恰恰是由于没有彻底“儒化”(用您的话说),所以现代化才没有受到阻滞。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儒家就是新加坡现代化的动力。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想听听您的看法。
杜:很好,你的发问层层逼入,气势非常恢弘。我简单谈一下《新加坡的挑战》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认为通过宗教可以使新加坡的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新加坡社会对宗教非常敏感,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最怕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李光耀在国会里对吴庆瑞提出质疑,很多华裔也不接受。吴庆瑞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有没有介绍儒家伦理的可能。当时在台湾讲儒学是很政治化的,其他地方也没有相应的参照,吴庆瑞就到美国,找了八位儒家学者。我是被邀请者之一,也是唯一拒绝的人,我觉得新加坡和儒学没关系。后来,吴庆瑞在纽约安排了一个座谈,我受邀参加了座谈。我发现,吴庆瑞真诚地希望儒学能像其他宗教那样在新加坡发挥作用,因此我同意参加他的计划。八个学者中,我是最晚到新加坡的,作了两个演讲。其中,英文演讲他们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然后译成中文出版,这就是《新加坡的挑战》一书。可以说,我在没有对新加坡作任何实际调查的情况下写了这本书。由于我的提议,在那之后的十年间,新加坡建立了一个东亚研究所,以研究儒学为重要议题。我给他们提了一些建议。首先要弄清问题意识。儒家和现代化,儒家和现代发展,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韦伯的问题?其次是实证研究,也就是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中儒家伦理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是,这些讨论与中国大陆有没有关系。第四个问题是,儒家与世界的关系。为了处理第一个问题,我邀请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者,包括埃森斯塔、皮得·伯格、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等,从韦伯的思想入手进行研究。
后来,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根据联合国的组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对中国的香港、台北、上海青浦,日本某地,韩国的首尔受儒家影响程度的研究,结果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其次是日本,然后是中国的香港、台北、上海。当时日本有一百个学者受文部省的资助研究儒家价值和日本的发展。后来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作了一些研究。在此前后,有一个日本学者——他同时也是美国驻日大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日本特殊论”。当时有些人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是由于日本不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本和西方的关系远远大于和东方的关系。但是这位日本学者批判这种观点,他在1974年就提出,假如日本的成功和它的核心价值有关,例如它的工作伦理、储蓄率、团队精神,那么中国的香港、台湾、沿海地区,以及新加坡都会发展。如果越南能够和平,越南也会发展。如果中国大陆能够跳出计划经济,获得经济动力——这个动力和日本以及“四小龙”有相同的地方,中国大陆也能发展。后来,人们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等。当然,东亚金融风暴后这些问题又不谈了。
你刚才说的很重要,儒家伦理作为“心灵的积习”不是提到反思层面的观念,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习俗。这些习俗有两面:一方面,东亚人工作就是勤奋,储蓄率就是高,团队精神就是强;另一方面,就是贪污腐化,就是公私不分,企业和政府就是勾结,就是没有透明度。是不是把儒家的“心灵积习”切断了以后才能发展,还是通过使它的正面力量发挥大的作用就能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有一种信念认为儒家和小农经济、家族制度、专制政体结了不解之缘。这是发生学上的观点。但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却没有小农经济的心态,有没有可能呢?新加坡受到儒家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不是小农经济呢?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首先是对政府的理解,西方自由主义有一个非常强的观念:政府是必要的罪恶(necessary evil),所以要限制政府、控制政府。但是东亚社会很奇怪,都认为强势政府是好的,唯一的例外是香港。有学者认为,它是“放任经济的典范”。香港人认为这是荒谬的,他们认为香港奉行的是“主动的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ference)。事实上,香港政府对香港经济的调控是非常周密的。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都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为这些社会造成了很多与现代性不符的东西。其次,这些社会中的非正式结构(informal structures)影响比较大。比如中国大陆的经济,除了见于数字的经济还有很多没有见于数字的经济。乡镇企业是什么样的经济实体,人们现在还不清楚。比如说,一个大学也可以作为经济体系到处投资,在美国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乡镇企业既不是集体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私人企业。它公私不分,但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在中国大陆,企业精神最好的地方是浙江。浙江的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进入第二代很困难,但家族企业还是家族企业,它也能够全球化,比如温州人的餐饮业,巴黎的华人餐馆几乎都是温州人办的,四川政府也在纽约办了几个餐馆,这在西方是不能理解的。在“非正式组织”中,礼的问题事实上比法的问题更重要。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东南亚集资的方式,上亿的资金在一天内就可以集起来,完全没有契约,只靠相互之间的诚信。还有一点就是教育,教育成了民间宗教(civil religion)。在东亚,人们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的程度在西方社会是不能想象的。再有一点就是家庭。很多人认为孝道已经没有了,我也赞成。但是有一位叫杨国枢的社会心理学家在中国台湾作过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他把“孝”分成“孝思”、“孝念”、“孝行”。调查的结果发现,在中国台湾社会,“孝”仍然存在。
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使人们成为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西方信仰宗教和个人的人格发展是什么关系?罗蒂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的自我完成(self-realization)和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完全矛盾。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整个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我认为,罗蒂错的可能性更大。
东亚的现代化确实有它的特性,这些特性需要作更深的调查研究。我现在回应一下你提出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性研究”还在进展中。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不能采取因果关系的视角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发展和儒家文化提供的动力之间的关系。吴大猷曾经指出,儒家文化和现代化之间不是必要关系,否则非儒家文化地区现代化就不能发展。另外,儒家文化也不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否则清代中国就可以发展现代化了。儒家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是其他类型的关系。对于第三个问题,我认为,两方面都有,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既是儒家文化促进的结果,也是排除儒家文化阻碍的结果。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高薪养廉、设立廉政公署等抑制官员腐败。对于第四个问题,显然东亚那些成功的企业的主要知识背景是现代的而不是儒家的。但是,如果从他们个人的深层理解上看,比如李嘉诚,他说:“我不是什么儒商,但是别人说我是儒商,我听了以后觉得也不错。”另一例子是印尼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到哈佛讲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我觉得非常惊讶,他讲的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后来问他,他说:“我看了你们的东西。”所以,这里的文化认同问题很微妙,东亚的企业家们过去没有认为自己是儒商,但是看了儒家的东西后却希望做儒商。我可以确定,在日本,从涩泽荣一以后,日本的企业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们有意识地在发展儒家。比如,三菱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出身于汉学世家,三菱公司几十年来一直支持“东洋文库”。对于第五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修补启蒙的缺陷”、“另一条路”、“现代性的他者”和我们谈的“多元的现代性”之间有些问题需要澄清。有两个问题我们值得一问。第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可不可能存在没有传统的现代性,比如说法国的现代性和法国的传统有没有关系,美国的现代性和美国的传统有没有关系,等等。美国的现代化和西欧完全不同。从欧洲到美国是一个断裂,不是一根而发。因此,就有现代化是否可以具有不同形式的问题。可以说,从实证上看,现代化具有西欧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等等。
衣:我之所以不愿意用“多元的现代性”这个术语,是由于美国、德国、日本的现代化虽然是不同的形式,但是作为它们的本质核心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说“多种表现形式”、“多种类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多元”就变成了不同的东西。“多样化”和“多元化”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多样化”是说本质上一致的东西具有不同的表现,“多元化”则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杜:我也一直在考虑是用“多样”还是“多元”。我们就用你说的“多样”,“多样”意味着西方启蒙所代表的推动现代化的精神永远是一个主导的过程还是逐渐被转化?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大问题。所以我不用“修补”这个词,面对人类的大问题,各种不同模式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发展和原来历史上发展的西方的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包括西方一些杰出的学者所考虑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假如中国发展出一套和西方有很多不同的现代性,包括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市民社会,那么由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造成的差异性和作为现代化社会必须具有的和西方社会的趋同性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
衣:我想问的是,假如中国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现代性,那么它是同传统社会的差异大呢,还是同西方的现代性的差异大?
杜:绝对是和传统的差异大。
衣:那样的话,它还是回到了启蒙的核心精神中。
杜:不一定。启蒙的核心精神和西方的传统的差异太大。启蒙的精神决不是从“两希”文明中发展出来的,它的断裂性非常强。还有另外一种极端的说法,西方的突破(breakthrough,或者说breakout)是一条不归路。过去没有人质疑,现在西方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却在质疑这条路是否正确。以前的现代化是一根而发,甚至可以划分出现代化的不同阶段。现在面对人类生存的问题,人们思考的是还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境。
衣:关于东亚现代化,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您二十年前在新加坡做的实验在今天所要经历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我认为,是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信息化对“80后”、“90后”的影响会很大。这种信息化的力量是可怕的。任何全球化都不可能把本土文化连根拔掉,但是信息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的趋同性会非常强,传统的根基在他们的知识中会越来越少。他们的知识是自主构造的,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非中心化的”。他们从网上获得知识,在网络里,没有历史和现实的差异。这些人将来会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讨论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
杜:现在的“年轻文化”确实使得“杂交文化”问题非常突出。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交谈。信息化使世界变得“天涯若比邻”,同时也使得“比邻若天涯”,人们宁可和遥远地方的人谈也不和身边的人谈。
但是,每个人在选择性增强的同时,对根源性的感受也越深。任何人都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有他的性别、种族、语言、出生地、年龄代、阶层和信仰等。现在人的选择越来越大,比如,我做中国人的意愿越来越小,我愿意做加拿大人、美国人,在政治上的选择也很多。但是这些选择和人的地域有复杂的关系,比如说黑白的关系,不能说全球化的趋同使得所有黑人都愿意做白人。以前有个“大熔炉”(melting pot)的观念,现在美国人也不提了。“大熔炉”是把其他少数民族都融入到主流,实际上是一种宰制性。以前,在中国台湾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台湾本土”,但是现在讨论的人很多。全球化和地域化、区域化是同时进行的。麦当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衣:麦当劳不论怎样“地方化”,最根本的配方还是麦当劳。
杜:但是,“全球化的地方化”还有另一个方面,比如日本的漫画,还有印度的电影。那么中国将来能不能发展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但却是中国的东西。
衣:不论日本的漫画还是印度的电影更多的还是现代科技理性的产物,而且如果没有大众传媒作为依托,它们没法“全球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启蒙的延伸。
杜:这个确实有。但是我想不讲西方,也不讲美国,因此当你从“西化”变为“现代化”时已经把地域性淡化了。你说它们是科学技术、科学理性的发展,我赞成。科学理性、科学技术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体现得就比美国更好。
衣:但这样一来,还是回到启蒙的核心精神上了,还是启蒙核心精神的开出。
杜:启蒙的核心精神(自由、理性、人权)和他者(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公正、同情、责任等核心价值是不是可以形成对话?这个对话是不是“启蒙心态”所完全包容的?哈贝马斯之所以在欧洲不如解构主义影响力大,就是由于他还抱着德国的理性主义代表的启蒙。他晚年的时候和罗尔斯谈启蒙,他们的谈话中就是开不出“自然”和“天道”。面对21世纪,以下四个层面应同时考虑: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启蒙的四个价值分别是自由、平等、效率、团结。这四种价值中完全没有自然和天道的位置,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如果把自然和天道放进去,这个人文主义就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凡俗的人文主义是启蒙的体现。我认为,启蒙的问题不是修补的问题,是对话的问题。应该慢慢地出现对话的文明,学习的文明。
衣:在强调文明的对话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达成共识。实际上,我反复谈到启蒙的核心价值,并非强调启蒙的核心价值是西方的特权,其他国家只能照搬照抄。我完全同意应当动员精神资源修补和发展启蒙与现代性,我只是强调,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具体的任务。对于启蒙可以进一步挖掘出来的内在精神资源,它们本身具有对启蒙的内在的反思和修补机制。而对于启蒙的外在精神资源,例如,儒家伦理,无论它如何优秀,如果不能在全球化背景中找到与启蒙的具体的对话和互动机制,都不可能对启蒙的自我完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实际上,我认为,迄今为止,所谓用儒家伦理来发展和修补现代性,更多地还是少数学者圈子中的理论命题,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它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很大影响的精神资源。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把这些精神资源罗列起来,而不探讨具体的相互作用的机制,不仅对启蒙的反思无补,还可能带来实践上的消极后果,这就是:我们可能既没有建立起与现有启蒙核心精神不同的另一种现代性,又放弃了启蒙精神中的一些积极的和肯定的精神资源,把自己的现代性完全局限为地方性知识。如果有机会能够对您所提到的包括亚洲、美洲等在内的其他一些本土精神资源进行深入探讨,揭示这些外在的精神资源如何能够同启蒙构成本质的关联, 或许对我们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启示。
本主题前一文章
|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杜维明 衣俊卿 --- xinmaopai006 2009/09/06 00:11 (17891 by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