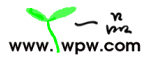王占阳:社会主义自由化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发表于 2010/07/25 09:08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我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发表后,李悔之先生写了《王占阳教授:这种“曲线救国”思维要不得——评王占阳教授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认为我这篇文章是“曲线求国”之作,并质疑“违背极为简单的政治常识,甚至不惜颠倒历史的事实去追求我们本来应当堂堂正正、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东西,这种手法是否可取?” 李先生的文章是善意的,我的这篇答复也是善意的。我想告诉李先生的是:您在某些方面不了解或者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曲线求国”,而是在实话实说,“直线求国”。我希望所有对我有此误解的朋友都能理解这一点,更希望朋友们能对我的话的内涵能有一些比较确切的理解。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就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化”
李先生不赞成我在文中阐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化”这个命题,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命题正确的,因为它是有历史根据的。
欧美19世纪的自由化,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的自由化。譬如,那时的选举自由,就是这样。当时欧美先进国家对于选举人都有性别、种族、民族、财产、受教育程度等等多重限制,其结果,自然是几乎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富人及其追随者才有选举权,因而也就几乎只有他们才能享有自愿投票或不去投票的选举自由。这种主要为少数富人及其追随者所享有的自由,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因而从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的历史过程及其成果,自然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些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不是人为虚构的,尽管当今华尔街的控制者实际己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按照我们的阶级理论同属“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公众公司(而不是资本主义公司)的高级雇员了。所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确实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我们知道,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恩格斯晚年才着力领导了争取普选权的历史斗争。
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自由仍然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因而李先生以这种自由不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为由反驳我,实际只是一种误会。
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在文章中已经讲得相当明确:
“西方的某些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实际已经程度不同地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瑞典等国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就更是这样。一切造福人民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马克思早就预言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大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事实,也基本上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不能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的出现和发展,这对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
不仅如此,我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如《认真学习借鉴美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等等)中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现代西方社会己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了。我最近在美国还说过,把美国这种社会命名为“资本主义社会”,实在是莫名其妙!对此,美国学者也点头认同。所以,我认为,西方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化(包括实现普遍的选举自由)的巨大进步,因而把西方现代政治自由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已非常脱离实际了。
总之,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不成立,也不是我有意“曲线求国”,而只是李悔之先生不了解我在世界社会主义方面的主要观点,因而也就误解了我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内涵。
二、争自由、争民主确实是共产党的活儿
李悔之先生说:
“我说王占阳教授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思维,或许有人会为王教授鸣不平。那么,我们再来看王教授下面一段话:
‘但我们知道,真正的共产党从来都是要自由、要民主的。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真正的共产党也都是坚决主张新闻自由的。反自由、反民主,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儿,争自由、争民主,才是共产党的活儿。’
历史事实果真像王占阳教授说的那样吗?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相继诞生生几十个共产党政权,有哪一个共产党政权“是坚决主张新闻自由的”?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吗?注意,不能将‘坚决主张’与现实行动当成一回事!
‘国民党反动派’又果真像王占阳教授所说的那样糟吗?对此,共产党的老朋友诸安平先生一席话就极能说明问题:‘在国民党治下,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但在我看来,李悔之先生又误解了王占阳教授。
请李悔之先生注意,我在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当然是“真正的共产党”吧!那么,《共产党宣言》是怎么说的呢?《宣言》里讲得很明确: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就明确了:只有为普罗大众争自由、争民主的政党才能是真正的共产党。反自由、反民主的政党则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无论它们的自我标榜究竟是怎样的。
这同时也就明确了:争自由、争民主确实是共产党的份内的事;而反自由、反民主也绝不是共产党的活儿。
沿着这个思路,高放教授曾经在原苏东各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上精辟地指出:
“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实际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既反‘苏’又反共。
‘苏’ 者苏维埃,就是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工农政权机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靠工农创造的苏维埃顺利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又在宪法当中规定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苏共长期以来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是在苏共政治局几个领导人作出决定后再强加给苏维埃,有些决策甚至瞒着苏维埃。
除了反苏,苏共还反共。共产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党时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十月革命之初,苏联还是存在民主的。但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就处心积虑地开始个人集权,到1941年终于把党政军三大权力集中于一身,之后又推行了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这些做法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主义色彩。斯大林确立的这些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高放:《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恩怨》,《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
毋庸置疑,既然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既反苏又反共,那就意味着苏共那时就已名存实亡了,即已不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共是这样,其他同类政党当然也都是这样。所以,李悔之先生以这种假共产党不搞新闻自由来证明真共产党也不搞新闻自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谁是掌握了政权的真正的共产党?我认为从为全民特别是为普罗大众争自由、争民主的角度看,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是很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概念的真共产党,而且该党至今仍然在党章和实践中将自己定性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那么,瑞典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不是在实践中始终维护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再就中国来说,所谓“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这也是一种绝对化的概括。
国民党里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独裁派),也有国民党革命派(民主派),本身就不可一概而论。国民党反动派里面又是有相对温和的人(即在政治上主张专制制度,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向往现代文明的那些人)和杀人如麻的反动军阀之分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内的某些人士(如蒋介石)又程度不同地扮演过多种角色,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作为落后国家的政党,中共也不可能成为比较纯粹的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从主张自由民主到主张封建法西斯主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有如光谱一般序列存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而由此所决定,中共实际也存在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其中当然也包括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并不是只有向以“四人帮”等人为代表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方向演变这样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共党史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都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全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七大”确立的建国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共确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准备实行军队国家化,参加全国大选,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而且当时中共党内也确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真诚地主张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等党的重要领袖和高级干部。
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道路,实际也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并不是只能走后来的苏式和毛式道路的。譬如,刘少奇就曾在1951年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选举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重要思想,他说:
“我们不熟习搞选举,党内也不熟习,不习惯,这是不好的。最近北京郊区搞选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村干部选不上,原因是不少村干部疲塌、消极、强迫命令、贪污腐化。过去对这些人搬掉一点就哇哇叫,说是‘卸了磨子杀了驴’。现在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选掉,你没有办法,老百姓不选你,因为不保障选谁。村干部提意见,说选了反革命怎么办?选了反革命,让群众吃点亏以后不再选就是了。保障人民的选举自由使石头搬掉了。搬掉了你,你在党内还要检讨,为什么老百姓不要你,要检讨一番。选举要很好的搞,这也是为建设作准备,没有人民民主不好搞建设。最近发现东北的贪污分子多和商人勾结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在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选举就整风、批评,这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过去我们把它忽视了。”(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5日)
显然,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中国的民主自由就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发展起来。但刘少奇的这篇重要讲话遭到了毛泽东出尔反尔的激烈批评,刘少奇被迫做检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自由民主的道路也随之中断了。但这并不等于这种中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譬如,如果毛泽东在1948年的轰炸中光荣了,刘少奇成为了党的主要领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就有可能按照刘少奇等党内民主派领导人的意愿相对较好地发展下去,尽管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毋庸赘言,在这种矛盾中,刘少奇干的是真正共产党的活儿,毛泽东干的则不是真正共产党的活儿。但是,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没有公然批判和否定过民主政治。就此来说,近年来有人公然站出来向民主政治大泼脏水,实际不仅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而且同时也是彻头彻尾的反共言论了。
由此可知,我并没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没有说严重背离事实的“违心话”。我所说的,实际都是大实话。
三、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化
李悔之先生要我“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再谈‘社会主义自由化’”。这个要求在逻辑上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它同时也表明,李先生对于我的学术思想实在是太不解了。
实际上,正如许多读者都知道的,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我提出和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 的基础理论,著有《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06)一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仅在互联网上就可查到至少20多万字的有关论述(如《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等文都在网上)。李先生说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其实心中也是一片茫然的”,这只能说明他的功课做得还很不够,甚至连到网上搜索一下我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的简单工作都没做。作为一位评论家,这显然是过于草率了。所以,我建议李先生以“王占阳 社会主义 普遍幸福主义”为题在网上检索一下,这样就能很方便地了解到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也可以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无谓评论。
关于“社会主义自由”问题,我在2004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初版)一书中,实际也已基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命题,作出了如下阐述: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自由原则。自由是公认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核心也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社会主义所讲的自由,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社会公众能够普遍享受的自由。这种普遍自由,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自由。社会的普遍自由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只是因为它是公民普遍幸福的一个基本源泉。自由,从根本上来讲,实际是人类的一种天赋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也曾谈到过 ‘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2]‘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得到满足,人就会产生幸福感。所以,如同富裕一样,自由也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基本来源。自由的对立物、否定物,就是专制、统治、奴役和压迫。因此,如果说自由是幸福的源泉的话,那么受统治、受奴役、受压迫则就是痛苦的源泉。如果说自由是基于人性的文明状态的话,那么统治、奴役、压迫则就是人类的一种野蛮状态。恩格斯讲,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其基本理由之一,也正是在于它同时又伴随了人类从自由的文明状态到野蛮的压迫状态的历史倒退。现代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要推翻阶级统治社会,最终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取消,其基本动机也正是在于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普遍自由、普遍幸福的新社会。所以说,社会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天然的社会自由主义,就是普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有规则的普遍自由,就是要实现有规则的社会主义自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邓小平语)实际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自由化。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从来都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当年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也只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短暂的过渡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更强调的,则仍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广泛、最充分的普遍自由。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如果没有人民的普遍自由,而是大多数人仍然处于受统治、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那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所以,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要把人民从形形色色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是要满足人民对于自由的普遍需求,就是要使人民从普遍享有的各种自由中,切实地感受到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实际上,这段话就是我在《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自由化”的原始出处,而且其中已经包含了基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命题而给出的基本论证。
在这个问题上,这里还应说明,社会主义有应然的社会主义与实然的社会主义之分,社会主义自由化也有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与实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之分。所谓应然的社会主义就是应当实现但仍未实现的社会主义,所谓实然的社会主义则就是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由此,所谓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应当实现但仍未实现的社会主义自由化,所谓实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则就是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自由化。
当我讲到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应然的社会主义,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自由化”更是首先是指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而我国距离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主义,还远得很呢!我强调“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中国逐步实现,而并不是说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自由世界了。
当我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我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应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并不是说中国的现状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因为,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只有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时,“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说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说现在己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后来把“建设”二字去掉,似乎中国现在已经是“特色社会主义”了,这就极大地歪曲了邓小平理论的本意,极大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导致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我们也应按照邓小平的本意使用这个名词概念。我认为,中国现在不仅没有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更存在着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的极大危险。
我相信,只要李先生看过了我的主要著作和主要论文,了解和理解了我的学术理论,他的评论就会比较客观、公允了。
四、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不是虚幻的
李悔之先生说:
“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最起码的一条是要逻辑上能站得住脚。下面,且看王占阳先生一段话:
‘应当承认,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化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化基本上只是少数人的新闻自由化,并不是普遍的新闻自由化,因而也就并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化。只有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化才是全体公民共享的新闻自由化,才是真正普遍自由的自由化,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化。’
可爱的王占阳先生:‘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这个‘巨大的社会进步’,既不存在于过去,更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王占阳教授的主观臆想中。既然如此,‘应当承认……进步’之说从何谈起?——还在酝酿之中、大字还不见一撇的东西,就‘应当承认’比别人‘进步’了,这也太‘马列’了吧?”
但李先生这种理解并不符合我的本意。因为我在文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这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的现实性:
“最后,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必然会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新闻自由相接近,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西方的某些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实际已经程度不同地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瑞典等国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就更是这样。一切造福人民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马克思早就预言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大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事实,也基本上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不能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的出现和发展,这对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都有它们的社会主义共性。所以,出现了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又有了自己的新发展。”
什么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譬如瑞典的新闻自由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
关于瑞典社会的性质,我在回答[西方牛]网友关于“如何看待北欧的福利政策。有说人他们更象社会主义”的提问时曾经明确说过:
“不是更象社会主义,而是已经建成了有人家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从经济角度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剩余价值已经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而被人民所占有。这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直接改变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但其所达到的结果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路径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而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应根据它的结果来肯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北欧人民是否普遍幸福,这一点早有公论。”(《与人民网网友深入对话大国崛起与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2月8日)
显然,这种社会中的新闻自由。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闻自由。
关于现代西方的社会性质,李悔之先生也在文中说:
“社会主义理论在19世纪20至30年代在欧洲兴起之后,人类为之探索、奋斗了一百多年。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许多不声不响地为此目标而奋斗的西方国家,目前却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显然,从逻辑上看,既然认为人家已在整体上“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就应当认为人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因而也就不应认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既不存在于过去,更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王占阳教授的主观臆想中”了。
李先生,究竟是我的逻辑不严谨,还是您的逻辑有暇疵,您是不是可以再判断一下?
再就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也不是虚妄的,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在我国逐步推进的现实历史进程。这就是我在文中所说的:
“近30年来,我国社会的自由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也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人民正在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成就。如果按照过去的言论标准,现在的13亿中国人统统都是右派。如果今天这个会是在‘文革’时期召开,那么,会还没开,展江教授就得被抓起来了。即使侥幸开起来了,警察也会冲进来把我们大家都抓起来。‘文革’时期有新闻自由吗?没有!那时只是主张新闻自由,就得面临蹲监狱的危险。‘文革’时期有新闻监督吗?也没有!那时的报纸、广播、杂志只有照本宣科、洗脑灌输、奉旨批判、粉饰太平的义务,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监督的权利。自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曾经为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神圣之物,已被无情地妖魔化为了资本主义的坏东西。代之而起的,则就是张春桥之流的‘全面专政’。同那个时期相比,我们现在真是应当感到庆幸!我们从近30年的历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的自由化,人民的自由化,新闻的自由化,这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李先生似乎认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是不可兼容的。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却己在相当的程度上实现和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可兼容性。诚然,在苏式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兼容性也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对这种政治体制实施根本改革,才能比较充分地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有机统一。中国的最佳出路,既不是坚守苏式政治体制不改革,也不是搞激进主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应当实现党的领导与现代民主政体的有机统一。虽然这种根本改革非常难,但它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因而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充分兼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己经不能展开了。
五、自由民主究竟有没有“主义”性?
李悔之先生说:
“自由,是天赋人权。她是不分阶级,不分‘主义’的。民主,是我们应当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
我不想在这里陷入复杂的论证,只想简要地说: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平等、博爱等等基本价值本身没有任何“主义性”。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就是民主、法治就是法治、人权就是人权、公正就是公正、平等就是平等、博爱就是博爱……。它们首先是人性的内在要求,进而又是时代的内在要求。
但人们对这些基本价值享受范围的选择却是有“主义性”的。“主义”是标志着重要价值选择的范畴。价值选择既是主观的,也是现实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等等现代基本价值的享有范围存在着重大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基本上只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富人及其追随者所享有。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又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究竟是只让少数人享有这些现代价值,还是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这些现代价值,这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价值选择,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用以标志这种价值选择的一对范畴。
“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本意是指主要为少数资产阶级富人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所以它是不完整、不彻底的自由、民主。完整、彻底的自由、民主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
“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意则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这就是完整、彻底的自由民主,亦即概念中的自由民主。
所以,在自由民主前面加上“主义”限定词,这不是空洞虚妄的,而是有其很重要的实际内容的。人们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老词儿,但却不能否认它所指称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
但若把虚假的自由民主叫做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而把真实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叫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那就更荒谬了。
在这种混乱之中,有时直接使用“普遍自由”、“普遍民主”这些名词概念,确实可能更好些。
但在争取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的过程中,有时使用“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名词概念,显然也更有利。
“社会主义”不是空洞无谓的概念。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尽管“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并已被严重地沾污了,但只要经过适当的界定,这个名词概念就仍然是可用的,也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主义”既是标志着重要价值选择的范畴,那就意味着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永远都会有“主义”。重要价值选择是不可能消失的,“主义”也是不可能消失的。讨论“主义问题”,实际就是讨论重要的价值选择问题。西方“主义”繁多,首先是他们的价值理性发达的一种表现。这是先进,不是落后。现在有些国人厌倦了“主义”,想要抛弃一切“主义”,则是从一种误区又走进了另一种误区。如所谓“没有主义之分,只有民主与专制之分”,就是忘了“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之分,“少数人民主”与“普遍民主”又是一种重要价值选择,因而也就是一种“主义”之分。这些朋友想与国际接轨,却又想抛弃国际通用的“主义”一词,岂不怪哉?“主义”一词的涵义都没弄明白,就想抛弃一切“主义”,岂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最后,特定的重要价值选择实现、完成后,相应的“主义”话语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与考上大学后考大学就不再是一个价值取向和现实议题完全是一个道理。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实现后,“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名词概念自然也该进历史博物馆了。但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尽管我们也可以用“普遍幸福主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等等名词指称相应范围的“社会主义”,但要抛弃它的真实内涵,却是做不到的,除非是我们背弃了这些普世价值,这些“主义”性的内容就永远会在我们的头脑中缭绕。
总之,“主义”绝不都是空洞虚妄的,而是通常都有其重要的实际内容的。“主义”话语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李悔之先生也在文中使用了“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名词概念,而且是有其实际内容的。我是认真地对待“主义”话语及其真实内容的,而不是在用“主义”话语兜圈子、玩策略、“曲线求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是真诚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也是真诚地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的,这才是我的真面貌,也是我从不掩饰也无需掩饰的真面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