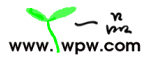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发展的幻象》前言:发展、知识、权力
许宝强 发表于 2009/11/15 06:40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许宝强
发展主义(developmenl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系列类似沃勒斯坦(1.Wallerstein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丁的重要课题。收编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新鲜的事物。质疑“现代化”或“工业化”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声音,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虽然大力抨击发达地区(或中心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的剥削,使后者不能发展,但在根本上它并没有否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论是提出脱钩(de—1inking)或依附发展,依附理论学派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并没有质疑如何使欠发展地区(边缘地区)成功地增长经济财富这类议题(参阅Arain 1990,Evans1979,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附理论于80年代日渐式微,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有关。尽管东亚四小龙均在颇大程度依附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技术,但它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却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而又不愿掉进自由经济学的窠臼,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概念,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政府有效干预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的功绩(Amsden 1989,Wade 1990)。然而,这种对自由市场发展学院的批评,基本上仍是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并以追求有效的增长方法为最核心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还是陷于发展主义的范式之中。
经济增长的迷思
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见沃勒斯坦文章),但却被看作为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
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严格来说,这些经济指标均以货币作为量度单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个被界定的经济体内年度的货币流通总量。不过,这些指标却经常被看作能同时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增长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究竟涵盖什么?反映了哪些经济方面?又掩盖厂哪些生计活动?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质量”吗?
这些指标是根据某年度内生产出来的货品和劳务以货币衡量的价值,要通过贸易流程,才可以被汇总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之内。因此,那些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从而未能被货币衡量价值的产出及劳务,例如主要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和育婴工作,或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又或是朋友、亲属之间的互惠活动,或是志愿组织的服务等,均没有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之内,因此家庭妇女、农民和志愿工作者等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
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西欧18—19世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大量妇女由农村或家庭走向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则进厂工厂,但更多的妇女则投身服务业。以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例,约四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从事女佣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换句话说,妇女由从事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转到收取工资的女佣岗位,提供的虽然也是家务劳动,然而这转换却奇迹般地使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
19世纪的英国并不是惟一的例外,战后美、加、澳、英等地,随着世界经济急剧膨胀,大量妇女投身劳动力市场。女性进入市场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 25%~40%上升至1990年的60%一68%,其中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则由1950午的10%一20%上升至1990年的45%一60% (Snooks 1994a:15)。
国民生产总值在统计了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余,并没有扣除她们因而减少在家庭或农村的非工资劳务时间,因此高估了妇女就业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妇女的非工资劳务对社群的贡献非同小可,据斯努克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资劳务占澳洲总体社群收入(市场工资总额加家庭非工资劳务)的35.8%,而联合同欧洲经济委员会更估算非工资劳务所生产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James 1994:173)。
这引起了另一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同民经济增长时,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移,结果是原来在非货币经济中没有被算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或劳务,在经挤货币化后却被算入指标之内,,从而高估了工业化或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在统计上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偏好,不单对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造成错觉(见下文),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业化或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仍然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程度,结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增长”。
此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是以总数或平均数算出,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地区或相同地区内不同人口之间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组织在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时,只能将不同国家的货币折算为一种通用货币(通常是美元)才可进行比较,但在折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汇率,却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或“低估”的现象。有人曾计算,1960年至1984年间,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扩大,有三分之二是由汇率的实际变动所造成的(Wood 1991)。换句话说,实际汇率的变动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变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以货币量度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地区或国家之内,倘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的增长与两极分化同时出现,那么对大部分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采用凰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亦会鼓励较贵重但却不一定是必需的产品的制适。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却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因为较贵重的产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而产品价格下跌却对穷人有益,因此这些指标明显带着不平等的偏见。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但对拥有固存财富——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带来的福利排除在计算以外。举例来说,若我们今年购人一部新的电视机,但同时把旧的抛掉,结果是新购的电视机的价值被加入国民生产总值内,但被抛掉的旧电视机的价值却没有在计算中扣除,结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对自然财富(例如空气、饮用水、森林等)的计算。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内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大量伐树)、对饮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学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对空气的污染(减少林木将减少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级市场购买“蒸馏水”或购买飞机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气,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又或是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来,只有购买昂贵的设备以清除环境污染,这也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值。换句话说,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
同样的逻辑亦可应用在人类环境的计算之上。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也会像机器般“耗损”(depreciate)——视力衰退、消化系统破坏、思想退化等,但这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也不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不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耗损”而兴建的医院和增聘的医疗人员,则被算进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结果人类健康的破坏也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参阅Anderson 1991:21—28)。
塞林斯(M.Sahlins本书第二二章)更进一步指出,所谓资产是财富,越多便越好,这种观点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原初社会的采猎部族。当采猎地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差不多耗尽时,采猎户必然迁移。换句话说,游牧是采猎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维持生计。然而高流动性却与积累资产不能并立。对终口迁移的釆猎部族来说,资产只会变成负担。一方面,采猎部族面对的物质压力相对地轻,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随手获得,当食物(野兽)或水资源渐竭时,只要转移到另一处地方,问题便能解决,,因此,对采猎者来说,并没有必要建立库存,积谷防饥;另一方面,不断迁移使携带资产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轻装上阵才能令采猎户的转移流动舒适方便。为了使迁徙过程顺利,部分采猎户更会刻意毁坏其所“拥有”的大型 “资产”,甚至把不能移动的老弱伤病“人道毁灭”。对采猎部族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资财,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然而,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的物质生活是否便十分匮乏,处于绝对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若从人的欲望无限,但却受有限资源制约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答案才会是“对”的。不过,欲望(特别是对物质的需求)无限中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建构,并非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的满足绝不必要透过不断拥有财富来实现;减少对物质资财的欲求,往往能使欲望容易满足,而后者正是原初采猎社会的经济逻辑。循此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是制造贫穷的源头:若贫穷的意思是物质资财的拥有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么强调(甚至鼓励)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不无时无刻制造贫穷的。相反,原初社会的部族民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因为在他们特殊的社会背景(采猎经济)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求,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容易获得满足的。在一个不以积累资产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原初社群,“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是从数量上计算福利,但“质”的改变,例如宁静愉快的心境,却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指标没有把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愉快的感觉考虑在内,因此倘若人们因为一些较苦闷的工作职位有较高薪酬而转工,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因而会提高,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些指标对闲暇(1eisure)的处理。当我们能够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生产出与以往同样多的产品或劳务时(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多出了的闲暇时间所带来的好处;但假若我们把多出来的闲暇时间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劳务时,却会引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好像“提高”了福利,反映了这种统计方法对闲暇的歧视(Anderson1991:29)。事实上,正如塞林斯指出,原初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消费品,但活在原初社会的人却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工作,因此闲暇时间较多,特别是一些居于拥有丰富资源的森林的采猎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时便足够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谈天等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因此,采猎民的生活质量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为差。
荒谬的是,在“闲暇”备受忽视的同时,“闲暇产业”却在当代蓬勃发展。高尔夫球场、迪斯尼乐园式的大型游乐场等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现代(富)人解决他们的“闲暇”问题。然而,这些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闲暇产业”,却背负着十分沉重的社会和生态代价。
超英赶美的幻象
发展主义另一个迷思是:所谓“落后”地区若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慢慢追上发达国家的。而有关“落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是论争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开出了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出口导向的药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以计划经济作为发展的启动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则倡议由“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策略性地扶助重点工业。然而不论是哪一个派别,多数都不反对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的条件。
将工业化(或所谓生产性产业、科技产业)置于经济增长以至发展的中心位置,是各类发展主义话语的通病,这种生产/工业/科技中心论,基本上忘记了经济活动其实是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或使用)等环节,而这些环节都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活动,当中包含了各类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脱离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文化社群活动和政治活动,纯生产或科技本身是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或更确切地说,从来就没有纯生产或纯科技的活动。
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东亚高速增长,为这种产业/科技中心论提供了新的养分,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的确凿依据,为新—轮的发展主义信念打了补丁。不过,过去十多年东亚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并非是由于政府以干预金融市场来集中庞大的资金对工业作高强度投资,以达到所谓“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导致的,而更多是与当地的大企业和政府垄断或操控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关。以日本的对外投资为例,1981年至1994年间,投资于工业的总值约是l150多亿美元,而投放在服务、金融、保险和商业的总值,则达1760多亿美元,若加上运输、地产、农业和矿业等非工业部门,非工业的对外投资总值差不多是工业投资的三倍;而这些地区近
日陷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并非所谓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技术受到限制,更主要是由于这种垄断结构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消费不足所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
以备受议论的日本经济为例,强调工业和生产领域的话语,只把讨论的焦点放在高科技之上,完全漠视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商社)在战后长时期获利和高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它们所建立的广泛贸易网苗和与政权的良好关系,从而得以垄断或部分垄断交换、流通和消费等市场环节,包括货运、保险、金融服务、资讯、广告、百货连锁店等。掌握了这些交易和政治网络,日本大企业便能够控制工业产品和各类劳务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企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接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的对外投资中,超过一半是以少数所有权 (minority ownership)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日本商社在外国的合资企业中,通常占有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大部分更是低于百分之三十),而外国的政府或企业才是最大的股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受到当地政府的投资法律(特别是想保护本土工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动以不拥有多数所有权的身份与外国企业合作,因为全资拥有虽或可较能保障产权,但却同时会成为某种负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绑在产业上”便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减低,风险增大。相反,作为拥有少数产权的合资者,日本商社能够较灵活地利用它们的投资,一方面可减少初始的投资成本,另一打面亦可降低日后营运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再者,放弃全权拥有合资企业,并没有导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权力下降;事实上,由于日本商社的经营主要以贸易为主,关心的是商品的流动而非固定资产 (stock)或实际生产,所以它们情愿把资金投放在建立广泛的贸易网络上,特别是在重要的世界经贸金融中心(如纽约、巴黎、伦敦、香港等)建立各种“商业基础设施”,包括仓储、海运、保险、金融服务、技术资讯等,以控制世界市场。只要能掌握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供求渠道和资讯,以及生产者所需的金融和商业服务,日本商社便不难控制合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并能获得远比生产/工业活动为高的利润(参阅Kojima and Ozawa 1984)。
2()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并非特例。回顾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可以看到领先者往往在—些环节(不一定是工业)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因此获得垄断的位置。而所谓发展竞赛,就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的垄断优势”。各种发展策略: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创新科技等等,基本上旨在利用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企图削弱对手的竞争能力,以确保自身的垄断位置。
对生产领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于对18—19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误解,以为工业(技术)革命确曾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以人均国民收入计算)的贡献并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与过去的经济增长率比较,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突出。根据他的估算,在1086年至1170年的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1801—1831年工业革命高峰期基本上差不多,而在16 世纪上半叶的增长率,更是工业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此外,牛津大学经济史范斯坦教授(C.H.Feinstein)最近重新估算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中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对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乐观估算,存在不少问题。他综合了—些新的资料后指出,在1778—1782至1853—1857这75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少于百分之三十,而在1830年以前的50年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工人需供养的人数增加,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居住环境变坏和公共卫生恶化,再加上社会福利补贴的减少,使得工人在工业革命这75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并没有大幅地为大多数英国工人带来美好的物质生活。而1810年间此起彼伏的工人抗争运动,正好从侧面反映工业革命对工人的负面影响 (Feinstein1998)。
不论是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以19世纪英国作为模型,而看不到更长时段(自16世纪甚至更早)和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历史,因而看不到18—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长周期过程中,资本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把资金投放到工业的一个结果。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性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消费不足,再导致工业生产“过剩”,进入了另一阶段的经济长周期低谷,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不是增长的灵丹妙药,更可能掉进发达地区把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给贫困地区的陷阱。
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因工资等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而将工业外移。这些新兴工业国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时期内互相竞争用作工业投入的资源,使工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又过量生产相类的产品,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下调,造成了工业产品的利润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把资金投放在金融资讯等第三产业,通过控制新兴工业国千方百计要争夺的资金,获取厚利。
伴随着低、中收入地区在60—70年代工业化的,也正是发达地区(特别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性工业的外移。据世界银行两位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自 1960年起,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占工业的份额持续减少。相反,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的污染性工业份额则稳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l—233)
因此,将工业化,孑经济增长紧密联系起来,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误会,正如将富有国家称为七大“工业国”,基本上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些所谓‘‘工业国”其实已越来越非工业化,越来越依赖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相反,低、中收入国家则越来越工业化。然而,正如塞林斯、沃勒斯坦和阿里基 (G.Arrighi)的文章分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均程度,不仅没有随第三世界地区的工业化而缩小,相反,在战后至今的数十年间,甚至是在过去 400年内,更有扩大的趋势。在1997年,富裕国家约占全球两成的人口,共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百分之—点三的消费(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研究报告》)。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80一90年代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不论采用自由经济的出口导向,或国家干预的进口替代式工业化;也不论是采取依附论所倡议的与世界经济脱钩或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以发展工业为目标的低收人地区的发展主义式的追求,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工业化只是在某特定的历史时段,对特定的群体,如发达地区的工业资本家有利,而往往并不是低、中收入国家用来超英赶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资本主义历史周期中,置身于良好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地区,才会获得资金的青睐,经济才会较快速地增长。然而这些幸运地区的人口,只能占全球人口的极少数,因为它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稀有资源的垄断和对大多数人口的排拒剥削之上才得以实现。这是维持哈罗德(Roy Harrod)所谓的寡头财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机制(见阿里基文章)。换句话说,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大部分人的贫困之上,无论低、中收入地区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实上,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1750至1950年发展了的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表面‘‘发展了”的国家,其实只是独享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经济成果,而这种享占,也不是个别国家的政策所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剩余积累从中心溶化开来的历史效果。因此,落后地区的“赶上”,只能意味着别的地区的资本积累衰减,损害他人的经济福利。沃勒斯坦更预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已差不多到达极限,难以为继。
发展主义者将发展过程中包括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社群以至偶然性因素,硬套为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强度投资等问题,只是在强化一种十分褊狭的习见;而自由主义、计划经济和“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之间的论争,由于将经济增长、工业化等视作理所当然,因此扮演着维护发展主义范式的共犯角色(见班努里文章),无法开拓新的话语空间。
...
不是结论:怎样办?
尽管循不同的进路、持不同的政治和学理,本文集的文章均对发展主义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质疑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合理性,挑战建构现代化发展话语的运作流程。可以说,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动摇了发展主义大厦的根基。
然而,对于是否要大厦倒下,或大厦倒下以后该怎样办,这些文章却没有达到统—的意见。这也许是值得欣喜的。事实上,我们也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惟一的出路。
较为激进的回应是班努里对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根本拒斥立场,认为现代化发展只为原住民社群添加麻烦,并没有实质的帮助。沃勒斯坦则认为反体系运动应该以争取在各地提高工资的方法,对资本主义上层构成压力,尽量保留工人所创造的剩余。这样,便可以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负荷过重”,大幅减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使经济资源上的分配更为平等。沃勒斯坦认为由国家政权推动的任何发展策略都只能是幻想,只有透过争取平等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发展。
相对于沃勒斯坦较为经济主导的关注,马格林和阿帕杜雷更多地关注“空降”的现代化发展对原住民社群性和既有存活方式的破坏,然而,不同于班努里,他们并不要求完全排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文集内其他作者在批判现代化发展主义之余,也没有接受完全排斥现代化的立场,只要求给予原住民的(不)发展模式和生计知识体系相同的地位。
埃斯科巴和邦克的介入点主要在话语层次方面,邦克希望建构一种新的、依据特定历史背景的发展模型,埃斯科巴则追求一种与批判西方发展模式的人民反抗结合的话语,“设法使用本地知识去改变既存权力筑构”。这种介入与帕帕特、阿普菲尔—马格林与西蒙的观点相互呼应。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强调这种新的语语应该加强第三世界纷杂多样的女性的声音。
尽管建议不同,但各作者异口同声提出了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的不信任。沃勒斯坦在文章的副题中问道:(现代化)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于在现代化霸权享有优越地位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发展专家,答案自然是前者;然而大部分农民、工人或原住民对这问题的答案,恐怕会大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