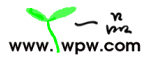组织的蜕变与危机中政府增长
马翠军 发表于 2009/10/27 00:57 一品 各抒己见 (www.ywpw.com)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再到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几乎每次危机都引发了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扩张。从有限政府到凯恩斯的大政府再到“几乎没有企业的哪个方面是政府不能干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语)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至于今天各国政府全面介入虚拟金融组织运行。人类社会致力于追求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最大程度不影响社会大众自由生活的政府,但每一次的社会危机,不论大小,也不论是哪个领域,都会引发人们普遍认同的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增长与扩张。政府权力整体上呈现为一个持续扩张的进程。政府在屡次的危机中被动提升权力,却又屡次被新的危机瓦解。人们对社会经济秩序的需求是否只能在政府增长过程中渡过?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前行,应付危机与政府增长将是人类社会秩序演进的基本路径。
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都会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引发人类认识上的历史阶段划分,但对于历史的认识而言,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凸显时代间的差异,也不是因为相互间存在不可超越的历史断层,相反,危机作为一个转折点往往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准确把握每一次社会危机发生的机理,并将一系列社会危机历时性串联起来,不仅可能把握历史的走向,更有可能理解社会秩序演进的逻辑。我们把每一次危机后的政府权力增长视为一种应急性的举措,但是它却往往成为下一时期社会整体治理方式的基本体现。这似乎表明政府增长存在路径上的依赖。政府权力按照某种模式增长和运行并不是政府本身所能左右,政府增长只能算是一种政府角色的转换,或者说政府增长其实表达的是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中政府角色的演进。如果说政府增长是社会秩序演进的需求,那么理解政府增长应当从社会秩序演进的角度来把握。而社会秩序这一宏大概念以及社会秩序演进这样的重大问题只能在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被解读。
人是一种组织化的动物。由于组织本身具有信仰、秩序与庇护的功能,人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成为组织的成员。当组织成为一种共同体并围绕共同体目标行动时,组织对外的势力扩张便展开了,伴随组织的强大与组织间冲突不断,人们需要对组织间的利益与权力进行协调与规约,公共权力就顺势产生了。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权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发挥作用。组织愈强大,对外扩张的要求越大,政府权力也就必然随之增长,而且,组织间关系愈复杂,政府的责任也就越多,政府权力也就随之不断扩张。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增长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增长,而且政府权力必然是作为社会组织权力(权利)增长的体现者。在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理性和效率不断降低权力和政治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并使大量财富在组织中得到合法有效的利用,但不断社会化的组织又成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扩张的基础,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政府权力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政府履行公共权力职能的重要性。在政府权力“削弱”与“强化”的双向同步走向中,恰恰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组织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政府增长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内在关联。
组织的蜕变与政府增长
人们对现代社会组织的认识基于斯密对社会分工的论述。但在斯密这位奠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基础的思想家那里,经济组织仍是一种简单雇佣劳动关系。他所谈及的经济组织基本上都是手工水平的简单加工组织,这一时期组织的简单性使其缺乏权力性和对资本、资源的占有性,组织与市场几乎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体。正如德姆塞茨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经济组织是“完全分散化模式”,“完全分散化没有给任何权威和控制的实行留有活动空间,尤其是没有给企业提供任何理论基础”(《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纬度》)。但大工业的推进使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特别的插曲”,自由市场竞争导致经济组织迅速向规模方向靠拢。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越来越成为经济组织轻而易举从自由市场中获取利益的奋斗方向。于是,规模经济组织或企业本身的控制机制和权威开始在自由市场中凸显出来,而建立在自由价格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则因为低效被规模经济组织逐步抛弃。现代企业的概念在这一基础上真正形成。
随着工业化和专业化企业组织的不断壮大,自由市场逐渐退化为工业化经济组织追求利润的基础和工具。经济组织在对资本与效率的追求中,不断在机器的帮助下延伸产业链条,努力使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支配整个行业,并使自身凌驾于自由市场之上。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本质上是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组织相对于完全分散化经济组织的胜利,这一组织形式演化的重大成果便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规模经济组织对自身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取代了对整个市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经济组织与自由市场机制逐步分离,进而走向对立,最终引发竞争的失衡和经济过程的中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从完全分散化的经济组织到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组织,组织在不断的蜕变中升级,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组织由无权威转向依赖权威生存的过程。因而也造就了政府权力的增长,以专业化经济权力为主导的政治竞争和大量行业化的产业政策滋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但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或对某一专业化经济组织培植和控制转向对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兴起的。凯恩斯宏观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依靠单一产业或行业控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推进了战后西方的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推进了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 并没有摆脱传统专业化、产业化的经济组织对整个经济秩序的影响,而是依赖它们进行综合协调。但是,经济组织形式并没有按大政府的要求沿着其固有的方向发展,而是随着不断推进的产业革命日趋走向分散化和社会化。经济组织逐渐摆脱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划分,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日益社会化。而依托传统专业化和产业化为政策依据的凯恩斯主义必然因此失去其原有意义。急剧膨胀的政府在迅速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中不仅不能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且在组织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步失去其自主性能力。政府越来越陷入价值规律指导下的经济波动,既不能消除积累过程的周期性紊乱,也不能有效控制替代性危机,从而导致行政行为强化经济危机。
摆脱这种局面需要政府从经济过程中抽身,让大量的权力和财富在组织中得到合法有效利用,增强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各国推进的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是重归有限政府理念的治道变革。而没有认识到这是社会组织蜕变中政府在寻求新的治理方式,完全不是在限制政府权力,相反新的政府治理方式全面超越了有限政府理念,不断追求更大的权力扩张,承担更大范围的社会责任。
传统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基于以下三个条件,政府—市场的二元分离、专业化官僚行政以及对经济最大化追求。伴随社会组织摆脱传统产业和行业的约束,社会整体结构扁平化,国家与社会重新融合,支撑有限政府理念的支柱性条件轰然倒下。各种社会经济组织成为直接面对国家和政府的治理对象。政府的监管任务前所未有地扩大,带动政府立法增多、公共机构增设、政府雇员增加,政府的权力范围也空前扩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组织和企业的任何生产环节都是政府权力能够触及的范围。如果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是对有限政府理念的否定,新公共行政则不是对其简单的否定,而是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超越。
组织的虚拟化与新一轮危机
组织的高度社会化以及组织与社会边界模糊,使组织构成方式不断脱离传统强调分工和集权的组织形式,由科层等级转向自由契约组合。社会化意义上的自由契约,不再是对权利的转让、占有和买卖,而是一种平等协作。使用权的让渡是程度问题,而授予权利的界定是缔约问题。个人与企业的契约因此便呈现一定意义上的主动性,投入品所有者可以将投入品一次性转让,也可以出租,也可以参与专业化协作,还可以多方面进行合作。如果说使用权的让渡和价格信息的传递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投入品所有者就有足够的理由与企业进行平等基础上的协商,并签订契约。确立在平等与自由基础上的契约,必然导致经济组织构成形式多样化、结构松散化。企业可能小到两个投入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允许企业链条扩展,它又可以大到整个经济生活。在这一意义上,组织与市场关系再度回归“完全分散化经济组织”时期的融合统一。
在自由契约下,经济组织由对权威的依赖转向对信用的依赖。组织本身对权力和权威的摆脱,使组织的成长空间空前扩大,组织构成方式在这一基础上日趋自由和多样化,并逐步向虚拟化的方向演变。组织可以没有固定的结构,没有层级和纵向集中,参与组织的各方边界模糊,松散联合,可能不存在正式的合同关系,而往往是“关系合同”。这种合同形式只提供一个行动和关系框架,对合同双方真实关系留下一定的解释空间。虚拟化组织具有应对外界的足够灵活性,组织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合同双方的信任、自觉性和较高的忠诚度,也就是说组织协作是基于信任和资源的共享。虚拟组织的产生使组织彻底实现了从依赖权威向依赖信用的生存方式转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政府监管权力的急速推进往往针对的是实体经济组织,而对刚刚出现的虚拟性组织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应变措施,这一方面促使虚拟组织拥有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努力规避政府监管的实体经济组织迅速向虚拟组织的运作方式靠拢,不断利用信用资源取代传统经济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对信用资源的获取、占有甚至垄断成为不断虚拟化的实体经济组织追求的目标。犹如当年垄断组织对权力的追求一样,虚拟组织对信用的追求也成为经济组织最为便捷的成长路径。对信用资源的占有量越大,组织越能够超越自由契约中平等合约间的相互制约,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由契约的运作机制获取组织最大化的赢利空间和发展空间。组织社会化进程中自由契约这种普遍的经济运作机制,越来越成为虚拟组织赢利和成长的手段与工具。虚拟组织对信用资源的操纵造成经济组织与契约化运作的市场相分离,从而再现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企业与市场的分离。最终造成原有经济秩序的失衡和经济过程的被迫中断。
当实体经济组织不断与虚拟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依赖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时,实体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可能意味着在反向推助虚拟经济膨胀。在持续的经济循环过程中,虚拟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缺失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运作就会陷入秩序空缺。这也就造就了今天各国政府不仅不对造成自由经济秩序崩溃的虚拟经济进行严厉惩罚,相反竞相对其进行救助的原因。
从完全分散化的简单雇佣组织到专业化的规模等级组织,到自由契约下的社会化组织,再到今天不断发挥其巨大能量的虚拟组织,社会经济组织在连续的自我否定中蜕变,组织的每一次蜕变都是一次新生和自身能量的重新聚积,造就了更大发展空间和更灵活的运作机制。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是新生组织能量的释放和对传统秩序模式的颠覆,并引发政府治理模式的紧急应变和政府权力的一路高涨。组织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自身的蜕变来不断玩弄市场、挑逗政府。对于这一次危机中的政府增长,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希望自己偏向社会主义,但站在让信用回归国家、回归社会价值体系的角度,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又必须在这一选项之外不得不选择让政府权力增长的新路径。
每一次危机过后的政府增长,都能展现出一个令人依赖的新秩序,但应当切记的是新的秩序形式不是政府造就的,而是组织蜕变和社会组织原则演化造就的,政府增长只是这种秩序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