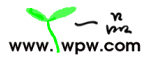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及其心理学预设
李义天 发表于 2011/06/14 03:50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在美德伦理学界,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者。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哲学系主任、现执教于迈阿密大学的斯洛特教授在最近30年间著录了许多重要文献,并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框架。由于他的努力与勤奋,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研究深度与影响范围获得极大推进,许多人都是通过斯洛特的作品而了解美德伦理学的一般特征,即,美德伦理学优先考虑“善”、“卓越”等美德论概念,而不是“应当”、“正确”、“错误”和“义务”等义务论概念;美德伦理学更注重对行为者及其(内在)动机和品质特征的评价,而不是对行为和选择的评价。[1](P89)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除非对斯洛特这样的活跃分子或骨干力量予以充分重视,否则就难以把握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而总是局限于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中。尽管斯洛特的美德理论不一定比亚氏更深刻,可这不代表他不值得关注,更不代表他的理论毫无启发。令人欣喜的是,国内已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斯洛特的学说,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依据斯洛特的新近作品与思想变动,对其学说予以评论,以期推动国内的美德伦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作为理论的美德思想与常识美德伦理学
自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M.Anscombe)1958年发表论文《现代道德哲学》以来,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呼应和提倡。许多重要的美德伦理学者,如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罗萨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等都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看法是:伦理学不是一门用于道德立法的理论,其主要任务不在于建立所谓的普遍规则,也不在于确立因规则而出现的道德义务。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典范的现代规则伦理学尽管言之凿凿,可是它们却相互冲突,导致现代社会对道德哲学的集体不信任。[2]因而美德伦理学认为,与其费力不讨好地把道德当作律法并塑造某种理论,不如回到伦理生活本身,关注行为者的内心健康及其人生成长历程。从而,伦理学也就应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那样,被理解为一种考虑优秀的内在品质、明智的实践推理以求实现幸福生活的思想。出于对规则伦理学“理论化”倾向的反感,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甚至认为,美德伦理学不但无需制造规则条文,而且不必把自己塑造成“理论”(anti-theory)。[3](P116-117)
虽然斯洛特在论及“关怀”时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4](P90)但是,他在这一点上显然没有威廉姆斯那么激烈。斯洛特觉得,尽管威廉姆斯指出规则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但却忽略了不诉诸“理论”所可能导致的问题:即,道德常识或道德直觉等“非理论”要素,自身是驳杂、冲突甚至充满悖论的,因此需要“理论”处理和修缮它们。毕竟,谋求思想的一致性和融贯性,才是哲学思考的内在诉求。所以,“虽然一种贬低直觉性伦理观念和现象的理论遭到反对,但是,只要我们打算获得某种不受悖论所困的理解,我们就真的需要在伦理学中确立某种理论,并且必须抛弃某些直觉。”[5](P183)在此意义上,斯洛特指出,建设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伦理学中是否需要理论”,而在于“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理论”。[4](P11)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如何通过扬弃道德直觉而完成上述理论任务,正是斯洛特的思考焦点。在那段时期的作品中,如《善与美德》(Goods and Virtues,尤其是1989年第二版序言)、《常识道德与后果论》(Common-sense Morality and Consequentialism,1985)以及《从道德到美德》(From Morality to Virtue,1992),斯洛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康德主义、后果论以及被他称作“常识道德”(common-sense morality)的伦理观念的局限性,确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道德直觉的常识美德伦理学(common-sense virtue ethics)。根据这条思路,斯洛特指出,康德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常识道德都存在严重问题,即,它们没有同等对待“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的重要性,都具有“利人不利己”的不对称倾向(asymmetry)。这些道德学说宣称,关注他人才是正确,而关注自我不值得肯定;相应地,没有善待他人是错误,但没有善待自己却不是错误。尤其在康德主义和常识道德中,道德义务的内容只是行为者应当关怀和善待他人,而与行为者自己的伦理价值无关。[1](P5)这个问题上,斯洛特认为美德伦理学更为胜任。因为“被我们的日常思维看作是令人钦佩的并且认作美德的,正是自我与他人的对称性。……(一方面)我们钦佩足智多谋、聪明睿智和审慎细心,即便这些美德主要是对拥有者自己而不是对别人有好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会钦佩有利于他人的品质,比如友善、仁慈和诚实,它们在我们的日常思维里也属于美德”。[5](P186)可见,如果“美德”是一个合理揭示日常道德思维的概念,那么“美德伦理学”也就当然是一种能够反映真实诉求、坦率提出“在利人与利己之间实现对称”道德要求的伦理学方案。
尽管斯洛特的近年作品主要给人留下一种与亚里士多德存在显著区别的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常识美德伦理学仍可被理解为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斯洛特甚至明确使用过“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常识美德伦理学”(neo-Aristotelian common-sense virtue ethics)这种说法。该思路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衔接关系至少存在两点:第一,两者都表达了对日常道德思维的尊重。斯洛特意识到,亚氏美德伦理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建立在古代人的某些直觉观念(比如,关于中道/适度的观念)的基础上,所以斯洛特也希望,“如果我们谋求一种美德理论,能合乎我们时代的直觉,正如亚里士多德为他的理论所谋求的那样,那我们最好诉诸我们的日常思维和直觉”。[5](P184-185)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反击康德主义和常识道德对“关怀自己”的贬低,以及功利主义和后果论对行为者个体价值的漠视。第二,两者都从“日常性”中提炼出“对称性”的道德要求。这一点正是斯洛特引以为豪之处,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伦理学,与其他的伦理学思路相比,不仅使我们更加关注那些关注自我的美德,而且将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两种现象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显得更相似,更像一个整体。在这方面,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和常识性道德都比不上它。”[1](P138)同时,“对称性”也属于亚氏美德伦理的基本特点之一,即,道德行为者展示各种美德,既意味着正确地对待他人和城邦,又意味着该行为者成就自我的卓越性。故而斯洛特断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强调根据利己的美德行动,又强调根据利他的美德行动,因而要比我所能想到的历史上的其他观点更加接近这一理念。”[5](P195)可见,在道德要求的内容方面,常识美德伦理与亚氏美德伦理具有相似性。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把该思路看作当代美德伦理学中的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二、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斯洛特的替代方案
不过,斯洛特很早(1992年)就意识到,亚氏美德伦理学尽管可以容纳“自我与他人的对称性”,但无法保证这一道德要求可以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中推导出来。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美德的个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人,即,他能够看出或识别出,在一定情况下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而这种说法清楚地表明,有美德的人做出光荣的或有美德的行为,乃是因为这件事是光荣的,而不是因为有美德的人选择了做这件事才使之获得了光荣的状态。因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行为的伦理状态并不是完全从品质特征、动机或个人这里引申出来的”。[1](P89)同时,斯洛特也注意到,西方伦理学史上其实还存在另外的思路,能比亚氏美德伦理更加彻底地揭示美德作为行为者内在品质和动机的核心意义和重大功能。[1](P90-92)1995年发表论文《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Agent-based Virtue Ethics”)时,斯洛特正式通过文章标题为这种美德伦理学的激进版本予以命名。
斯洛特指出,亚里士多德主义确实体现了美德伦理学的一般特征,即,理论聚焦之处不是行为规则,而是有美德的个人及其内在品质。但在亚氏思路中,一个人之所以有美德,一方面是因为,他能发现具体情境中的适度之处并作出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幸福”为大前提进行目的论的实践推理。在斯洛特看来,前者意味着存在某种独立行为者之外的“正确”或“善”,而美德之人不过是那种能发现它们的人罢了。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主义把评价行为的最终尺度绕过“美德”而挂靠在“幸福”上。可是,“幸福”是关于生存状态而非内在品质的概念。不仅如此,就连内在品质本身的伦理属性也需要通过“是否有助实现幸福”这种近似后果论的命题而说明。这样,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就很难摆脱“后果论”的指责。
于是,为了实现一种更纯粹的美德伦理学,斯洛特试图完全从内在品质出发,以行为者为基础来建构理论。在他眼里,“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就是把道德行动或伦理行动的状态当作完全从独立而根基性的动机、品质特征或个体的美德品质中推衍出来的东西。像这种基于行为者的思路,至少在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准解释中是找不到的”,它“明确地代表了一种极至或激进的美德伦理学类型”。[6]自此以后,斯洛特在1997年与马西亚·拜容(Marcia Baron)、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等人合著的《三种伦理学方法:一场辩论》(Three Methods of Ethics: A Debate)以及2001年出版的《源自动机的道德》(Morals From Motives)等作品中,日益强调这种美德伦理学的内涵及其合理性。
根据这条思路,正确的行为既不是由于行为者依赖外在规则,也不是由于行为者顾及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不是由于行为者发现了当前情境的适度之处,而是因为它源自行为者的恰当动机和优秀品质。更具激进意味的是,这些品质之所以“优秀”并配称“美德”,也不是因为它们像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认为的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人生目的,或者像康德主义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实施道德立法,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合乎直觉地令人钦佩(admirable),可以兼容人们关于最佳道德方案的日常思维,即自我与他人的对称性。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是通过“幸福”来论证“利人又利己”的必要性,那么,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所考虑的则是,如何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中推导出“利人又利己”的对称性要求。而根据内在品质的不同,斯洛特将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划分为三种类型:作为内在力量的道德(morality as inner strength)、作为普遍仁慈的道德(morality as universal benevolence)以及作为关怀的道德(morality as caring)。它们代表了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针对上述问题的三种回答。
“内在力量”是斯洛特对于健康灵魂或强壮心灵的描述。他以尼采思想为例,表明一个拥有内在力量的行为者,能够通过高贵的心灵力量而利他。因为这种力量使之具有“向外”展现自我的能力和倾向。于是,利他行为也就成为该行为者实现自我的证明,从而兼顾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关注。[4](P22)但斯洛特也注意到,从内在力量推出利他行为,主要不是出于对他人的体贴、同情和将心比心等温暖的(warm)心理动机,而是出于上述那种自我依靠的意志力。后者尽管高贵,却略显冷峻(cool)。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把作为内在力量的道德称作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的“冷观点”,而把作为普遍仁慈的道德和作为关怀的道德称作“热观点”。因为“仁慈”与“关怀”两种品质都十足意味着行为者替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因而,以此为动机,将首要地表现为令人温暖的利他主义。与此同时,出于仁慈或关怀而行动的行为者,也能够通过利他的举动而增进他们自己所关心的伦理价值。[5](P227)所以,作为普遍仁慈的道德和作为关怀的道德同样有助实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称。
三、从道德情感主义到道德心理学:斯洛特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对品质和动机的强调,无疑代表着斯洛特对人类心理因素的重视。同时,该伦理学认为单凭品质和动机便能成功处理道德问题,又意味着斯洛特对其背后的心理机制有充分认可。因此,除非知道斯洛特对道德心理的基本预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敢于如此激进而拒绝引入任何其他的伦理因素(如,道德规则、功利后果或幸福生活)作为基础。事实上,这也是斯洛特近年针对评论者的批评而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在2007年刚刚出版的著作《关于关怀和移情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及其相关论文中,斯洛特认真探讨了这一问题,即,如何通过对道德心理机制的合理说明,为内在品质和动机的道德有效性予以辩护。具体而言,斯洛特是通过三方面的工作来完成该任务的:(1)诉诸18世纪道德情感主义(moral sentimentalism)的资源;(2)汲取现代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的成果;(3)采纳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caring ethics)的观点。
如前所述,早在1992年出版《从道德到美德》时斯洛特就注意到,伦理学史上还存在将理论框架奠基于行为者心理的思路,其中尤以休谟为代表的18世纪道德情感主义为典型。休谟(有时也涉及哈奇逊、沙夫茨伯利)等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给予斯洛特的启发在于:
第一,他们同样将道德现象(言行举止、风俗规范)的发源地归于人的情感或心理要素。并且,他们都认为,一个现象的道德地位乃是由这些情感性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前者在道德上是否正确或高尚,要看它是否受到后者支配并反映了后者的诉求。而更为接近的是,比如哈奇逊和休谟,都直接把“仁慈”列为最核心的情感之一(在沙夫兹伯利那里,这种心理因素被称作“公众情感或天然情感”)。他们与斯洛特同样讨论了行为者因仁慈而利他的道德机制。
第二,他们尤其是休谟同样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称性”当作美德品质的一个关键判据。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清楚地写道:“个人价值完全在于拥有一些对自己或他人有用的或令自己或他人愉悦的心理品质。”[7](P121)“心灵的每一种对自己或他人有用的或令自己或他人愉快的品质都传达给旁观者一种快乐,引起他敬重,并被冠以美德或价值的美名。”[7](P129)这些断言不仅反映了休谟倡导世俗生活的主张,而且反映出他对美德的功能的理解,即,美德既意味着“利己”也意味着“利他”。
第三,18世纪的道德情感主义者同样认为,基于行为者心理因素的道德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在哈奇逊那里,行为者的动机根据受益面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从低到高若干层次,其中最高尚的动机正是斯洛特所提到的“普遍的仁慈”;根据该动机而行动,能在最普遍的范围内实现美好的道德生活局面。又如在休谟的道德理论中,作为道德发源地和评价尺度的道德情感,其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情感,而是被规定为一种可普遍化的、基于人类“共通感”心理机制的特殊情感。他说:“道德这一概念蕴含着某种为全人类所共通的情感,这种情感将同一个对象推荐给一般的赞许,使人人或大多数人都赞同关于它的同一个已经或决定。这一概念还蕴含着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是如此普遍如此具有综括力,以至于可以扩展至全人类,使甚至最遥远的人们的行动和举止按照它们是否符合那条既定的正当规则而成为赞美或责难的对象。”[7](P124-25)只要看看所谓的“共通感”和斯洛特经常强调的“常识”其实是同一术语(common sense),并且考虑到两者在具体内涵上其实存在互释关系,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休谟对于斯洛特的重要意义了。
然而,按照斯洛特自己的思路,他的思想应当要比上述道德情感主义前辈更加纯粹地“基于行为者”并且更加得到来自现代道德心理学的支持。
斯洛特坚持认为,他完全把美德当作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内在品质或动机可以说明其他要素,而它自身无须通过其他要素说明。相比之下,无论是沙夫茨伯利的“公众情感”还是哈奇逊的“普遍仁慈”,都以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公众利益或社会福祉为合理性依据。因此,两者的美德概念还不能堪称“独立的”或“根基性的”。而在休谟那里,由于他对美德的来源的看法被认为是多元主义的,即,“某些动机或品质特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给行为者和其他人带来了‘功利’,但是,另一些特征则以不同的方式让人当下就欣然同意(immediately agreeable),从而也被视作美德”,[8](P222)所以斯洛特不无失望地表示,由于“休谟似乎认为,动机的美德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功利性,依赖于它们给人们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我认为很难把休谟也称为一位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家”。[4](P8)
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美德的发生机制和心理基础的理解不同。对哈奇逊来说,人类之所以能够表现仁慈等美德,乃是因为人类具有道德感(moral sense)的官能,它如同味觉、触觉一样,属于人类的特性之一。虽然它是行为者的内在之物,但它反映的内容却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哈奇逊把包含着“最大限度增进福祉”这一后果论命题的心理诉求界定为美德,并命名为“仁慈”。而休谟则否认存在道德感。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表现得有美德,不是源自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被比喻为“类似味觉、触觉的东西”的官能,而是源于所有人的心灵所具备的一种受他人苦乐影响的普遍的心理倾向,即“同情”(sympathy):我们出于同情而能感觉到他人的痛苦,因此会激发仁慈的动机,想把他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于是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感觉而做出行为选择。[8](P223)
斯洛特接受了休谟的解释模式,即,通过心理运行的内在机制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美德的动机,为什么这些动机会导出特定的道德取向。然而斯洛特没有接受的是,他认为,当关怀和仁慈等情感作为动机时,其心理基础实际是“移情”(empathy)而不是休谟所说的“同情”,尽管休谟所谈论的“同情”“很接近我们所说的移情。但‘移情’这个词在20世纪才出现。它的德语词源(Einfuehlung)也是在20世纪才明确使用的”。[9](P5)所谓“移情”,是指一个行为者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上,把别人的感受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形成一种感同身受的情形。而“同情”则是对他人的苦乐有所感应和觉察,并因之反馈出相应的心理感受。斯洛特举例说:“我可以同情别人的尴尬,对此表示同情,而不必觉得像是自己遭遇了这种尴尬,从而也就没有对他人的尴尬进行移情。”[8](P227)由此可见,“移情”的心理机制要比“同情”更复杂——它不仅意味着识别他人的感受,而且意味着转移他人的感受。通过对他人感受的转移,行为者能对他人处境有更多体贴和了解,更能准确地置身其中并设身处地,因此更易做出为他人着想、以他人为重的行为。而近年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已证明,移情而非同情,才是关怀动机以及“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的原动力。[10](P223)
斯洛特对18世纪道德情感主义的扬弃,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他自己也承认:“移情作为利他行为之基础、支撑和必需品的这种作用,是在当前关于人类社会性发展的大量文献中才得到广泛讨论。”[9](P6)在心理学中,该观念被称作“移情—利他主义假设”(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11]根据这种观念,不仅做出利他行为是出自移情,对这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同样也出自移情。因为,评价者对行为者的利他行为表示赞许,就在于评价者把自己移到行为者的位置上而感受到行为者心中的暖意。所以,“赞许乃是对一个行为者展现给他人的那种温暖的移情式关怀的一种移情式的反应”,[9](P8)而评价者之所以移情到行为者那里时能准确感受并给予评价,同样是因为,评价者与行为者其实都有移情他人的心理倾向性。所以,移情的心理机制不仅说明内在品质如何推导出有美德的行为,而且试图确保人们在“关注他人是否应被赞许”等评价问题上相互承认。
四、结语:当代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心理研究
诚然,由于常识美德伦理学把核心命题(“自我与他人的对称性”)的合法性基础置于日常直觉,而基于行为者理论又更激进地认为“美德是完全独立而根基性的内在品质”,因此,斯洛特的这两条思路很容易令人感到不可靠,似乎他为了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极至性而不惜沾染上主观主义的弊病。关于这方面的担心,确实存在。但限于本文论旨,我将另外撰文予以讨论。在这里,我更愿意指出斯洛特美德理论的某些有价值的启发,即,他的学说及其心理学基础,典型地反映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于道德心理问题的重视,以及建构一种能够真实说明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机制的努力。诚如心理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很早指出的那样,“要了解我们伦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必须考虑描述心理学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12](P11)
实际上,当安斯库姆撰写那篇被称作“当代美德伦理学开端之作”的文章时,她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规则伦理学只空洞地保留了“律法式道德(即基督教道德学说)”的心理影响,而忽视了这种心理所赖以成立的文化背景。[13]而在另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献中,迈克尔·斯托克尔(Michael Stocker)则把规则伦理学的关键缺陷称之为“道德精神分裂症”(moral schizophrenia),即,规则伦理学所设计的道德心理与人们的真实动机存在隔阂。[14]种种情况似乎表明,当代美德伦理学对规则伦理学的发难正是从道德心理问题开始的。前者对后者的主要不满,就在于后者对行为者的道德心理过于简单化、强硬化、冷峻化的设定。
其实,就道德心理本身在伦理理论中的地位而言,它也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伦理学类型来说,只有为道德行为者设计恰当的道德心理,才能支撑该理论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同时,道德心理又是道德行为者的一部分,因此,一种伦理学将道德心理机制理解成什么样,它的道德行为者形象便会是什么样。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人们处理道德事务时的心理基础和运行机制,从而给出让人怦然心动的道德理由和运思路径,这或许是伦理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它甚至要比设计某种规范的生活方式这一任务更加紧迫!因为,首先,道德规范的内容决定权其实在于生活而不在于伦理学;其次,即便伦理学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道德蓝图并由此高喊“你应当”、“这是你的责任”等口号,但是,由于对道德要求的理解不等同于对道德要求的接受,因而也就并不必然导致好行为的出现。[3](P23-24)所以,如果伦理学真的要为生活着想,那么关键还不在于回答“我应当如何”(what),而在于“假如我应当如此,那么请给我一个好的理由”!该理由应该可以让我说服自己“凭什么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why)。在此之后,我才会进一步思考:“采取样行动以达到它”(how)。固然,美好的生活图景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我们更期待伦理学能够关心和体贴人,为人们找到通向美好生活的合适且有效的心灵桥梁。基于如上考虑,当代美德伦理学非常注重关于道德心理的阐释。而这方面的讨论也被统称为美德伦理的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 of virtue ethics)。它们当然同20世纪心理学语境中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道德心理学相关,但是,由于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的道德哲学背景,所以,它们依旧深具哲学色彩,代表着伦理学对行为者心理层面的说明和分析——正如我们在斯洛特这里看到的那样。虽然这种思考向度可能存在亟需澄清和辩护的问题,但是它绝非没有意义和前途的。因为这种向度使伦理学重新回到人本身,并使我们重新记起,伦理学原本就是诊治心灵的学问。
参考文献:
[1] Michael Slote. FromMorality to Virtue[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李义天. 麦金太尔何以断言启蒙筹划是失败的?[J]. 伦理学研究, 2007, (5).
[3]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 imits of Philosophy[M].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5.
[4] 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Michael Slote, Marcia Baron, Philip Pettit. ThreeMeth2ods of Ethics: A Debate[M]. Malden, Mass. : Blackwell, 1997.
[6] Michael Slote. “Agent - based Virtue Ethics”[J]. Mid2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20, 1995.
[7] 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8] Michael Slote. “Moral Sentimentalism and Moral Psy2chology”[A]. in David Copp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thi2cal Theory[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Michael Slote. “Moral Sentimentalism ”[J]. EthicalTheory andMoral Practice, 2004, No. 1.
[10] N. Eisenberg and P. A. Miller. “The Relation of Em2pathy to Prosocial and Related Behaviors”[J]. PsychologicalBul2letin, 1987, No. 1.
[11] C. D. Batson, The Altruism Question: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icalAnswer[M].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1.
[12] Franz Brentano. The Origin ofOur Knowledge of RightandWrong[M].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13] 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J]. Philosophy, 1958, vol. 33.
[14] Michael Stocker. “The Schizophrenia ofModern Ethi2cal Theories”[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6, vol.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