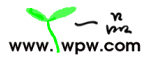中国语境下的施米特问题
高全喜 发表于 2011/01/22 09:46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卡尔·施米特在汉语学界的粉墨登场已经有一段时期了,围绕着施米特的政治法学,中国政法思想领域的各种阐释、比附乃至论争,在我看来,都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有着真实的现实社会政治的背景,是历史演变中的现实问题的一种理论表述,尽管不无歪曲和扭变。本文无意探讨所谓施米特的“纯学问”,而是试图考察中国语境下的施米特问题,在各种繁难歧变的思想扭结处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一、施米特的毒刺
关于施米特其人的历史小传,人云亦云,见仁见智,其实事情大致是清楚的,并没有多少迷雾疑团,目前各派的论述大多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意气之争,[i]尽管施米特一生的政治立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理论本身。毋庸置疑,施米特是一个充满毒刺的思想家,与那些自由主义的“善意的”批判者(如阿伦特、沃格林,乃至当今的斯金纳等)不同,甚至与施特劳斯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居高临下的”鄙视不同,施米特穷其一生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和充满恶意的,或者说,他的理论对手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学。[ii]
我们知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是自由主义的“凯旋史”。对于何谓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政治哲学,不说别的,即便是在自由主义内部,就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争论,变换了一种又一种形式,而且时至今日也不能说自由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已经定于一尊。传统的老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以及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晚近几十年来产生的各种后现代理论、施特劳斯学派、社群主义和剑桥学派的共和主义,它们从左右、前后两个方面不遗余力地夹击自由主义。但是,无可争议的是,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占据着主导地位,[iii]而且上述各种理论本身也都是在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所提供的言论自由的平台上各领风骚的,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在攻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它们共同的理论对手即是自由主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地位,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完善,甚至存在着重大的问题。
自由主义很少标榜自己是一种整全性的理论,可以包医百病,特别是20世纪的现代自由主义,如罗尔斯的理论,更是把自己降到了十分有限的公共制度领域,以至于成为“薄的”自由主义,只是诉求基本的“重叠共识”。即便如此,自由主义还是强有力的,在实践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理论上也是长盛不衰,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自身的自发建构性。首先,就理论层面来说,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尽管有各种形态,但主导的是英美主流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法学、宪政与政治理论,虽然其理论建构的形而上学不强,但也并非完全自生自发,而是随着时代问题的不同而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例如。古典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就包含着保守主义的诸多因素,格林、霍布豪斯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凯尔森的规范法学和凯恩斯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就包含着诸多国家主义的色彩,从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到现代的英美实证主义法学与政治哲学则一直保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特性,而现代北美的罗尔斯主义,既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趋向,又维系着洛克和康德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上述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是对应于西方社会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而产生出来的理论,在基本的法治社会、权利保障、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方面,则是大体一致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从总的精神来说,它们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之主导性的理论支撑。其次,就实践层面来说,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虽然出现过各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福利国家和所谓新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但就各个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来说,基本上落实了法治、宪政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峙以及现代的国际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架构。自由主义在政法制度层面和政治正当性方面,总是能够平衡各种内外因素引发的巨大震荡,在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攻击下,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宽宏的包容性。
勾勒上述这些简单的政治常识或宏观叙事,只是为了能够从世界历史的现代真实图景方面来审视一下施米特的思想。在某些人眼中,自由主义不过是些肤浅的经验之谈,平庸乏味,毫无新意,而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们远见卓识,识古察今,不是洞彻了人类五千年历史演变的隐秘教诲,就是揭纛了高于常态政治之上的决断国家命脉的内在机缘。但在我看来,真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面对人类政治事实的全貌,他们的高论华而不实,忽视乃至有意遮蔽了基本的道理,其实,政治之道往往是些历史的经验和简单的常识,是审慎而宽容的世俗智慧,在此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害人的。应该指出,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个施米特能够死而复活,在当今引起学术思想界的震荡,成为老右派和新左派共同的新宠,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而把他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考察,就更有耐人琢磨之处。究竟什么东西使得西方的老右派和新左派在施米特那里找到了共同的兴奋点,并不谋而合地夹击现代以北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乃至现实的政治制度呢?
就现实社会层面来看,西方社会20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律与经济方面的实践并非毫无问题,而是弊端百出,民主政治上的“公法化扩张”和“讨价还价的”民主的庸俗堕落,法律形式主义的冷酷无情和价值中立主义的不讲道德,经济个人主义的极端自私和全球经济过程的国际掠夺,这些都滋生于自由主义制度的机制之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就理论形态来看,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思想和解决新问题方面虽不乏创新,如伯林、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罗尔斯等人的各种理论,但并没有彻底地解决上述诸多的现实问题,而且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又不断产生分裂,一种普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念是否还存在也成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此,晚近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质疑日益凸显,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福山,冷战之后,他提出的以自由民主政治为归宿的历史终结理论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共识,反而遭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厉批评,由此可见,在今日世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基本价值并没有取得广泛的认同。从上述背景来审视施米特思想的复活就不难理解了,这颗毒刺为左右两派理论提供了解剖、批判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新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刺中了自由主义的软肋。
二、自由主义政治法学的软肋
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一直隐蔽着一个重大的主题(hidden agenda),[iv]那就是国家问题,在这方面,恰恰是传统的大陆法德国家的政治法权思想给出了深入的理论阐释。此外,英美的民主政治在20世纪也受到各个方面的挑战,现代的大众民主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出现了很多的弊端。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存在着所谓软肋的话,那就是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问题,实际上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挞伐最着力的也正是这两个问题,本文下面的分析将指出,在施米特眼里,上述两个问题其实是合为一体的,都是“政治”国家问题,即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无法为国家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国家的实质在于超越大众民主的非常态的主权决断。
施米特首先是一位宪法学家,他对于国家问题的看法,是从政治法学—政治神学的角度展开的。通观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如《政治的概念》、《宪法学说》和《宪法的守护者》、《政治的神学》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展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围绕着《魏玛宪法》文本的批判性考察。施米特通过剖析制定这部宪法的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基调以及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与妥协的情势分析,论述了他对于魏玛政治的认识。在他看来,魏玛宪政的平庸乏味与最终失败在于自由民主宪法的妥协性、价值中立和非政治化,问题的要害在于宪法第48条,即是否赋予了总统制以守护宪法的超越权限,对于自由民主的敌人实施专政。按照施米特的理解,魏玛自由主义政治法学的失误在于教条性地固守立宪政治的根本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不受公权力的侵犯,而不知市民法治国的基础在于政治国家,当宪法的自由民主实质本身受到侵犯时,需要一种国家的权威力量来保护宪法。
第二,构建了一套非常政治的宪法学说体系。施米特对于魏玛宪法的批判是基于他的一整套系统的宪法学理论,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宪法概念或理论,即绝对的宪法与相对的宪法,并据此划分了非常政治与常态政治两种形态。在他看来,相对的常态政治的宪法秩序是个别性的,非本质的,真正的宪法是非常态的宪法,在此,他提出了区分敌友的政治决断这个关系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围绕着敌友政治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集中对于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规范宪法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把他自己的宪法学体系纳入欧洲博丹以降的政治法学的宏大思想脉络之中来加以阐释。
第三,为了确立自己的政治法学的正当性基础,施米特并没有步传统的人民民主(直接民主)之后尘,而是返归罗马天主教大公主义的神学渊源,由此他与各种左派思想相揖别,表现出右派保守主义的底色。[v]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平等原则是一种虚假的理想,既不能防止不同利益团体的讨价还价的堕落,更不能为政治国家的主权本质给出正当性的论证,“现代国家学说的概念是从神学转换而来的”,从政治法学上升到政治神学,这是施米特法权学说的归宿,在那里,敌友政治的非常状态下的主权决断获得了最终的证明。
毋庸置疑,施米特的学说是庞大的、繁复的和“深刻的”,显示着一种德国思想的“政治成熟”。现在的问题是,施米特学说对于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一个权威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者?在我看来,尽管施米特问题是说不尽的,但他的思想确实刺中了自由主义的一个软肋,即国家主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及两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法政理论家:凯尔森与哈耶克。[vi]
施米特与凯尔森是直接的理论对手,施米特的很多著作对于后者是持猛烈的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法律观,尤其是宪法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在施米特看来,凯尔森的形式法学仅仅指出了常态政治的法律规范,其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纯粹的价值中立,即不愿就法律的政治内容给出实质性的判断,这样的法律尽管以维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但国家的主权实质性地缺位,民族国家的政治正义在凯尔森炮制的从国际法到国内法的规范层级体系中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决断。如果说在凯尔森的法律体系中国家主权还有一个纯粹的形式,那么在哈耶克的法律思想中,主权本身也被抛弃了,哈耶克在他的《立法、法律与自由》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主权”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怪物。[vii]有意思的是,哈耶克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是凯尔森形式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弱化,但他并不认同后者,反而在书中对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种立法的法律观凸显了国家主义的公法意志,对真正的自由构成了威胁。相比之下,哈耶克对于施米特明确鼓吹国家主权决断的宪法理论却未曾置啄。这是为什么呢?[viii]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现代形态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学所着力构建的是一种内政的宪政法治理论,对于对外主权的国家问题缺乏深层的思考,不是把国家视为一个既定的法律拟制(凯尔森)就是视为无用的累赘(哈耶克),国家法律的价值中立和个人主义的优先地位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哈耶克对于施米特的些许好感并非他的政治中心主义,哈耶克恰恰是要“政治的去中心化”(the dethronement of politics)的,而是后者的政治保守主义,即他们在反对实证主义的形式法学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民主的堕落方面,找到了共同点,只不过施米特诉求的是超越法律的非常政治的实质性决断,而哈耶克诉求的是自发演进的作为正当行为规则的自由秩序。但是哈耶克的问题在于,当自生秩序扩展到一个国家的边界时,国家之间的法权对垒是否可以抵御自由秩序的演进呢?对此,哈耶克并没有从宪法政治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说明,当然人们可以从他的自由经济理论中推演出经济规则的世界主义,但国家宪法的主权原则仍然被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凯尔森的法律层级理论却是补充了这个国家主权的缺位,由此可以说,他们在大的方面,都属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但问题在于凯尔森的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纯粹法学尽管逻辑上是自恰的,可在现实中从来就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学一旦走出国界(政治法权意义上的),就面临着言不符实的困难,这个困难在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中也是同样尖锐存在的,[ix]因此,这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软肋。
问题在于刺中了自由主义政治法学的软肋是否就一定证成了施米特理论的胜利呢?我看并非如此,这是本文在此所要着力阐发的,我们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按照前面的论述,自由主义政治法学的软肋在于国际间的国家主权缺位,其内政的宪政理论和规范法学无法化约国家外部的敌对关系,所谓永久和平只能是自由主义的一厢情愿,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和价值纷争决定了非常时刻的主权决断的必要性。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在国内法权关系中的绝对优先性呢?应该指出的是,施米特的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他把国家间的政治或民族国家的对外主权转换为一个超越于一切形式法学之上的绝对力量,把它的本质赤裸裸地解定为区分敌友,并一马平川地将其推行于国内政治。在他看来,近代法治国的两个法治原则——分配原则和组织原则,忽视了法治的政治要素,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国家的分权制衡来维护个人自由的宪政制度是无效的,因为,国家理由先于个人权利,国家不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显然,施米特的这个国家理由论与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后者看来,国家是由个人构建的,国家理由存在于个人权利的保障之中,固然国家具有法律的拟制人格,但它毕竟是虚拟的,而非实质性的实体,国家的对外主权不能转换为对内主权的绝对至上性,更不能以此来化约宪政的核心原则,即通过分权制衡来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学认为国内政治高于国际政治,内政的宪政原则高于外交的主权原则,人权高于主权。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第二,随着前面有关内政与外交的辩驳,其实已经涉及另外一个相关的重大问题,即究竟何谓真正的政治。在施米特看来,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就是有关主权的实质性决断,因此,自由主义法治国的两个政治原则——同一性原则和代表制原则,只是表述了常态政治的扁平状况,无法揭示政治的非常状态,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政治,在那里平时隐而不彰的主权作为一个极限概念张显出来,呼唤着主权者的决断。一切政治说到底就是区分敌友的非常态的决断,政治的实质就是非常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学与施米特相反,认为真正的政治不是非常态的,而是常态政治,政治最终要转换为法律规范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与民主,才能实现政治的和解。政治不是区分敌友,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法律上的权利平等和利益博弈。所谓政治,在自由主义看来,不过是通过民主的程序在法律的统治下实现个人的自由、幸福与其他诉求,政治需要树立权威,但那是法律的权威,国家需要一个主权者,但它最终要从属于人民,维护个人的正当权利。当然,政治并不总是常态政治,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非常态的时期,或者说也有非常政治,也有危机时刻,也需要统治者或主权者的决断,但那是特殊的,例外的,必须把非常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宪政制度和民主制度就是防止非常态政治绝对化和永恒化的政治机制。[x]施米特的问题是把非常态政治绝对化了,把所有的政治都视为主权决断的非常时刻,并且把这种决断的正当性付诸于神义论,因此排斥了自由民主的正当性根源。当然,自由主义政治法学无视非常态时期,遮蔽主权问题,否认政治决断的宪法学意义,也是教条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这样也就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出来了。其实,成熟的自由主义政治法学是完全可以把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规范政治与决断政治、法律自由与政治权威、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与权威相互平衡的政体理论,孟德斯鸠的市民法与政治法互动的法意思想,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的法律与政治国家的法律的统一理论,乃至当代宪法学家阿克曼提出的宪法政治与二元民主理论,以及自由派共和主义的商议民主理论,等等,都为应对施米特的非常政治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xi]
第三,应该指出,施米特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在15世纪以来的欧洲乃至北美的生成发育机制是带着德国思想的有色眼镜来考察的,这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清醒地把握到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民族国家所历经的艰难,甚至歧路,由此一脉相承地延续了所谓“德国问题”的本己经验和教训,并因此质疑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在德国实现的可能前景,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法学理论,以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成熟;但另一方面,他又囿于自己的本土资源而缺乏真正的审视世界的宏大眼界,他没有实质性地认识到英美国家在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民族国家所遵循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之正道。也就是说,宪政国家并非真的都像施米特眼中的魏玛民国那样软弱不堪和不讲政治,如果说他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法学的指责在魏玛宪法那里是深刻的和正确的,击中了德国自由主义的要害,但这种指责对于英美国家的宪法政治却是无的放矢,英美宪政国家在政治上远非如此幼稚和无力。尽管英美谱系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大多遮蔽了国家这个主题,以至成为“隐蔽的主题”或软肋,但在那里的自由主义宪政实践中,英美国家却从来都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政治从来没有软弱过,他们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胜利,充分验证了宪政民主国家完全可能是政治强大的,经济繁荣的,和人民自由的。那里的常态政治何尝缺乏政治的决断呢?那里的规范宪法何尝消解了自由民主的实质呢?那里的人权何尝与主权颉颃对立呢?
由此看见,无论就内政还是外交来说,一个政治权力有限度的强有力的主权在握的宪政国家是存在的,一个以法律特别是以宪法区分守法者(友)与非法者(敌)而不是以政治特别是非常政治区分敌友的法治国家是存在的。施米特以德国魏玛民国宪政的特殊个例来指陈自由主义的整个宪政实践,实在是盲昧于世界潮流的浩荡,至于他的投靠纳粹政权,则是误把杭州作汴州,不过是考量了他的政治智慧并不高明,而他晚年所炮制的所谓的大地法,尤其是游击队理论,则把自己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通过边缘的游击队战略来颠覆宪政民主的世界共和之大势,其左派先锋队的游魂已经瓦解了右派保守主义的风骨,难怪连施特劳斯也为之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