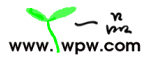牧惠: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书屋 发表于 2010/10/09 23:18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争好田、争坡水、争风水山坟、争松山、争草地之类纠纷时有发生,仅仅因为男女往来或唱山歌之类风流口角也可能引起械斗。客家人入籍广西较晚,同土人比较起来,在人数和政治经济方面大都处劣势。他们往往没有土地可耕种,又在械斗中屋宇被焚毁,变成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太平军或入伙别的什么组织。石达开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率领了一千多人到达金田村。韦昌辉的参加太平军,其中也有在土客之中被排挤想报仇的因素。
秦日纲(原名日昌,因避“昌辉”讳改名)“初为贵县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矿工”(《广西一览》,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39页)。他率失业矿徒千余人加入太平军。
胡以晃,“其人好高鹜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见《贼情汇纂》)。固平南鹏化山区一带山民之领袖,是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自有充分的势力者(《太平天国全史》第140页)。
……
以上这些人,或为流民,或与流民关系密切,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在当时的广西,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敲诈,大族欺压小姓,土客之争不断,加上人多田少,天灾人祸频仍,饥民充斥,饿殍载途,幸存者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土匪(包括在河道驾艇行劫的艇匪)、会党。这种情况,形成洪秀全、冯云山的上帝会最好的发展条件。还往往成为上帝会团结联络、依靠的一股力量。太平军积极准备举事时,加入队伍的有相当一批客家人,也有土人,都是被人欺负而不能安居于乡土的农民或游民,另一类是因为天灾挨饿的饥民,因为瘟疫流行以为投靠上帝教可以邀福免祸的贫民。土匪会党们也有加入了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全史》所引资料中举出的就有:
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等,广东鹤山人,活动于浔、梧江面的艇匪,最初曾投入太平军,旋脱离而降于清军;
罗亚旺,广东潮州府揭阳人,初在粤为盗,败入广西,为大湟江匪首。率部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
苏三娘,女匪首,拥众横行数邑,率部加入太平军,随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归太平军,旋叛去。
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中谈到,萧朝贵曾回武宣家乡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加入者有大湟江的天地会首领。
太平军打出造反的旗号后,沿途有很多人入伍,其中同样有游民和土匪。如打到永安时,吸收入伍的,有胡以晃弟弟以章率领的二千鹏化山民,有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还有梁亚介、范连德等土匪首领,分别率部加入,梁亚介一股达二千人。全州一役,太平军损失了冯云山,去湖南,又在蓑衣渡中埋伏,锐气受挫,损失严重。在道州,太平军广招各属土匪会匪及附义人民二万人来壮大队伍。此后队伍又不断扩大。在郴州,“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同时,又有广东仁化会党千余人北上来投。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从郴州出发攻长沙,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就从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六千人,其中包括土匪。在武汉,一批“为害与贼相埒”的潮勇加入了太平军。……(均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叶蒸云所著《辛壬寇纪》有关于太平军队伍不纯,大量流民涌入的记载。试摘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壬戌正月初八,……土匪勾引贼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发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惧其诈,移营城外。阅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贼镇守。
发贼……所领兵皆各县监犯盗贼之流,凶悍异常。
长发屡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赖者争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贼在太平说,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
贼以黄岩巨匪王明观为带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涨……(下面写王明观如何凶残)。
十二,长屿李小亨扬言进城。李本赌徒无赖,不能自存,降贼封附天侯。
(夏)宝庆,黄岩巨棍……。咸丰初,长发乱,官募乡勇……惟宝庆出应募。……宝庆在军带勇数百,日以抢掠为事,遂致富。夤缘冒功,官至都司,授宁波参将。……十一年,长发至天台,宝庆潜降。与黄、太两县巨匪会饮于新河,结为兄弟,号十八党,……。十一月初旬,长发至太平,先一日与徐大度、毛昌大、蒋国兴等纠众至县城,劫掠一空。长发至,又随之入。次日知各乡团勇将攻城,即遁归。入见贼酋李世贤。世贤索其妻子为质,为贼招陶宝登降。未几宝登逃,世贤怒,乘夜使人斩之,并杀其妻子及其队下数百。闻者称快。
(高)子风效弟(子诰,十八党的发起人)之所为,交匪徒,蓄乡勇。十月之杪,长发陷天台、临海,将及黄岩,子风与夏宝庆、徐大度以吊丧为名,聚众据县城,索富户,俟贼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
(《天国史事释论》第391—412页)
诸如此类的记录,满可以从有关著作中抄集成一个小册子。而且越到后期,这种情况越多。值得另提一笔的是,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说到,参加太平军的洋人如白齐文等,也是货真价实的流氓。“白齐文作过无数的诺言,结果却无一兑现。白齐文曾索取巨款,保证到上海去招募新兵,采购军火,取得协助,可是几经往返,他只带回了一箱箱的白兰地,使得官兵酗酒败事。……”(第533页)
...
三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改造谁?由于领导成员流民的成分很大,加上太平军一开始就缺乏正确的吸引群众的思想纲领,并无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些做法就往往与游民文化的习俗相同或类似。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不关心甚至破坏有关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就与游民那种流寇主义习性有关。其中一些做法,埋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谈到,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集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是刘、关、张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设誓共干一番事业。刘备对关、张说:“我独有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张为了表示决心,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第8页)
太平军的做法,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各地教徒,由近及远,或早或迟,或个人或结队,陆续前来团营。其在各地出发之前,必先变卖田宅产业,举家以赴。其卖不去的屋宇什物则尽焚之,多具破釜沉舟之志,大有义无反顾之慨焉。《浔州府志》纪其事有云:“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亦可见他们气概之盛与期望之大了。(原引谭熙龄:《紫荆事略》)
……凡全家入伍者,夫妻男女,即予分隔,妇女尽入女营,编制亦如男营。夫妻不得相聚,每星期夫妻准相见一次,相会时,有人监视,仍须远离勿近,高声谈话,不得喁喁细语,款款谈情。男女之防最严,犯者杀无赦(《太平天国全史》第204页)。
瑶族(还有客家)妇女不缠足,是强劳动力和战斗力,因此不曾效法关、张将她们杀掉;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相同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如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遭遇)看到,这些家属同时还起着人质的作用。后来,他们还把这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运用到战领的城市,实际上瓦解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同时也就无形中破坏了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王学泰在《天地会与通俗文艺》一章中用大量篇幅介绍游民社会中的隐语、暗号。在太平军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贼中讳字甚多,如火为亮,华为花,讳伪天父名也。督为率,基为居,讳伪天兄名也。国为郭,明为民,王姓为汪姓,讳洪逆父母名氏也。秀为绣,泉为全,天为添,贵为桂,名福为复,讳天逆幼逆之名也。至以考为老,镜为鉴,清为菁,龙为隆,光为洸,丑为好,卯为荣,亥为开,不知其命意所在矣。尝见改本梁惠王一册,首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闻者为之捧腹者久之。更有所谓三更者,逃亡之称也;变草者,投效官民之称也。即在天条十者之内,打水炮者,奸淫之称也;打先锋者,劫掠之称也;外小者,百姓之称也。如此类者不一而足
(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四,第438—439页)。
这当中有封建帝王的避讳规矩,有沿习两广的风俗,把一些发音不吉的词改为吉利(如舌〔蚀〕改称利,书〔输〕改称胜,肝〔乾〕改称润,空〔凶〕屋改为吉屋)的做法,如卯在粤语中读为“”即没有,亥读为“害”,因此改为“荣”、“开”。其余的则属游民社会中使用的“隐语”。不伦不类的修改令人捧腹者,不止一处。例如,“王”字已让太平军诸王所专利,“文王武王”于是改成“文狂武狂”,同样贻笑大方。
《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和最近揭露出来的“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曾经干过的“阿太”(瑞安土语中对此类巫师的叫法)一类迷信职业者当然也是属于流民。他们那种神仙附体,口出神言的装神弄鬼,在广西浔州一带称为“降僮”,在广西某些地方又称为“求仙”,完全是一套哄骗愚民的谋生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游民文化也传染到太平军中,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篇评介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文章竟说太平军“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叙比较可信:
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此时二人闻悉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兄弟等有记录其较为重要之辞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秀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谓:“此等辞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
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之言。杨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萧朝贵则以耶稣之名传言,而其言则比秀清之言较为和蔼。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上帝会;其言即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
又有许多患病者借祈祷之力而得痊愈。传言杨秀清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由记录上观之,则秀清似是自愿且祈祷将病者之病传诸其身,赎去其病,借使其人得愈,其后自己乃求除病。(《太平天国》六,第866—867页)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开始时“降僮”是未定身份的“有人”,洪秀全从中选定只有杨秀清、萧朝贵才是真的也即是可信的;内容也很驳杂,包括为人治病的原始降僮,最后发展到上帝会的一种天父下凡教导万民的思想工作方式。《天情道理书》说:
戊申岁三月,天公大开天恩,亲身下凡,出头作主,出头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姐妹乃合天下万郭(国)人民,……。
指的是一八四八年三月杨秀清在紫荆山“传言”,教导大家不受妖言所惑,不为敌人所吓,在洪秀全、冯云山被迫离开的困难情况下,坚定信心一直干下去。这时,“传言”虽然是一种落后遇昧的产物,客观上仍起到一定可怜的积极作用。
但是,越到后来,杨秀清的“传言”的消极作用越强烈了。杨秀清可以“突言天父附体,指其人所行何事,立即讯服,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轻则斩首,株连累累,时兴大狱,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群丑畏悚”(《太平天国》三,第46页)。再进一步,就发展到使用这种手段来修理他加意防范的韦昌辉,“诡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石达开“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太平天国》三,第48页)。对于洪秀全,也不例外。《天父下凡诏书二》记录下杨秀清以天父名义让天王受杖四十,并教导洪秀全,“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等等,逼使洪秀全作出“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的保证。(《太平天国》一,第34、35页)洪秀全杀人,也被责:
东贼伪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太平天国》四,第720页)
最后,就是伸手要万岁了:
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同洪秀全比,杨秀清对太平军的贡献确实更大;谁当第一把手更好,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他竟使用了这种露骨的愚蠢做法夺权,确实利令智昏,同时也是流民本性的大暴露。洪秀全尽管昏愦,也不难看出这番“天父传言”的用心所在,内讧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场内讧即火并的做法,也全是流民的手法,远远超过梁山泊上的火并王伦。《太平天国全史》引麦高文通讯载:
天明时,东王府内外尸骸堆塞,血肉遍地。其受伤未死者,亦狼藉伏地。“肯能”等浴血出走,践尸而过,曾亲见东王遗尸亦在府内。维时,暴徒蚁聚——乱抢、乱争、乱打、乱杀、乱叫——秩序大乱,杀气冲天。附近兵民纷拥入东王府,乘机抢劫,所聚珍宝,为之一空。又“有一大群人塞满外边院子,等候着那些在府内抢了东西携带赃物走出来者。府内之攘夺与府外之争斗,不管践踏男女、伏尸及受伤未死者之上——情形惨不忍睹。”(拙译载《逸经》33期)
如此滥杀无辜,不仅使得石达开等人震惊,更严重的是整个太平军失去了对上帝教和天父传言这些“神”的伪装的膜拜,上帝教基本丧失了原有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功能。
由此可见,流民有助于太军的组成和起事,流民又是促使太平军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当然,流民起事如朱元璋也有成功的,为什么洪秀全不如朱元璋,那又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