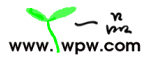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我们一家和薄一波一家
四人帮 发表于 2009/11/19 03:44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破碎的家
1972年,让我出来做点工作了,我立即找到一个出差机会前往北京。尚奎一再盯嘱,这次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大难不死的老朋友,看看那些不幸逝世的朋友的遗属和遗孤。又特别交待,一定要打听一波的下落和他的孩子的情况。其实他知道,他不说我也要做的,他是在强烈地表示他对朋友们的思念。
到了北京,我三下五除二地把工作干完了,随即先后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这时,我已知道一波还在监狱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波和明姐的大女儿安安。安安告诉我,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到外省插队,小七则下放在大西北……听着听着,我的心都碎了。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被“四人帮’,搞得家破人亡;孩子们星流云散,无家可归。
我强忍眼泪,又问一波的情况:“这些年你去看过你的爸爸没有?”
安安摇摇头说:“自从他被关起来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他们不准我去呀。”
“你去找过他们没有?”我又说,“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国民党的大狱还允许家人去探监哩!”
安安愁苦地对我说:“水静阿姨,前些时他们找过我一回,把爸爸的手表给了我。”安安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爸爸被他们害死了?也没办法打听。”
“不会的。”我说,“如果你爸爸不在了,一定要注销户口的。”
安安说:“你不知道,阿姨,爸爸从坐牢那天起,户口就没了。”
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着急了。可仔细一想呢,又不像。因为一波真有不幸,造反派会幸灾乐祸;而且要交遗物,也不光是一只手表呀,总还有点衣服什么的。一波是个富于智慧的政治上极为机敏的人,他肯定知道了林彪“拆戟沉沙”的消息,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势上的变化。他送出一块表,是让孩子们放心,他出狱有望了。我把这些想法说了,又对她说:“你现在要千方百计和你爸爸联系上。去找上面那些人,写报告,天天去缠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见爸爸,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有从牢里放出的叔叔阿姨,也要去打听,好知道爸爸的下落。”
可伶的孩子,一直在温暖幸福中生活成长,何曾经历过如此劫难?碰到这种变异,自然束手无策了。听了我的话,总算是得到一点安慰,有了一些主意。我回来对尚奎讲了上述情况,他很感叹!但和我一样坚信一波还活着。
水牢春秋
自从林彪摔死之后,老于部的艰难处境有了一些好转。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和尚奎对。一波的担心,稍稍缓解了一点,可是仍然为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而不安。
1975年的春天,我再次出差到北京,很快就打听到一波已经出狱,住在国务院西直门外第一招待所。于是我立即和安安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和刘勇(原炮兵司令员邱创成的夫人,是胡明那个局的一位处长)马上就看他。
“爸爸虽然放出来了,但还在受监视。”安安说,““去看他的人都要详细登记,不知搞的什么名堂。”
“登记就登记好了,我不怕!”我说,“死都死过了,生个病也就是那么大的事!”
“还是少点麻烦好,水静阿姨。”安安这孩子成熟多了,她说“我看你们不要去‘一招’,明天上午我把爸爸接到我们单位上来,你和刘勇阿姨9点钟来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事,时间我可以定。”
我觉得安安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她的安排。次日上午,刘勇带上火腿,我提上水果,准时赶到安安工作的首都医院,找到她那间小得可怜的房子。才坐下谈了一会儿话,一波那魁梧的身形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劫后余生,恍若隔世,我和刘勇一人抓住他一只大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刹那间,眼前浮现着他在狱中所受的磨难,胡明的被害,以及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别夫离子,十几个“女犯人”住一张通铺,失眠之夜的种种回忆……我已经无法控制积在眼眶中的热泪了。
还是一波心胸开阔,意志坚强,他微笑着,让我和刘勇坐下,慢慢说话。看着他的笑容,我的心像被刺了一刀似地流着血,在他的微笑里,含着多少悲愤,多少哀伤啊!他失去了一生中最最珍贵的夫人,我最亲密的明姐。
“这么些年了,你们都好吗?家里人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道。
我和刘勇都简要地说了一下各自的遭遇,我还代尚奎问候了他。
“也活下来了,算是幸运的。”我说,“你可受罪了,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也活下来,不过活得很艰难。”他苦笑着说。
我说:“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开头是些红卫兵娃娃对我搞逼供,那还好对付。”他说,“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说娃娃们,我做白区工作时你们还没出娘胎,怎么会知道那时的事呢?我役有当叛徒,倒是杀过叛徒。于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上政治课,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我的历史毛主席最清楚,问问他就行。”
我说:“是呀,真要去问毛主席倒好了。”
“后来换了些年纪大的造反派头头来,可把我整惨了。”他叹口气说,“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那套办法,就像历史上一班残忍的酷吏折磨屈打成招的老百姓一样。”
一波说,那些人成天要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他当然不会去写,没事就在房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或者倒在床上睡会儿觉。他们火了,把他关到一间一个多平方的小杂物间里,床撤了,只有一桌一凳,供他写“交待”用。他有什么可写的?困了,伏在桌上一样可以睡大觉。他们咬牙切齿,把凳子也拿走了,要他站着“写”,他更不会写了。白天,他在原地踏步,活动筋骨,地方小,也不能捆住他的胳膊腿呀!累了,他就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呼呼大睡。造反派暴跳如雷,大骂他“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挖空心思来计算他。那些家伙把小桌放在房子中间,四边不靠墙,而地上又放了一尺多深的水。使他既不能下地踏步,又不能倚墙而睡。但他还可以坐在上面闭目养神,或者打个磕睡。不过,这的确把他搞得疲惫不堪。有一回累极了,身子失控,竟从小桌上摔了下来,倒在水中。他那么大的块头,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造反派们便哈哈大笑。这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指示:不准变相刑讯,必须改善被关押者的生活环境。
“这以后,我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一波苦笑一下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我写‘交待’,我还是老办法;一字不写。他们变着花样审讯我,我就是一句话,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你们问他去!他们没招儿了,狠狠地说:‘好吧,你就坐牢吧!’我想,坐就坐吧,坐牢我还有点经验、”
其实,哪像他说的那么轻松!他遭到的无止无休的批斗、殴打、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在二七车辆厂,他被用橡皮上的铁条、木棍打坏脊椎骨,腰都伸不起来。有一回,因为理直词严驳斥了造反派的诬陷,被康生派去的20多个打手拳来脚往,打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拖回牢房。他还曾被四条彪形大汉分别抓住四肢,用力向上抛去,然后落在水泥地上,当即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冰凉的冷水之中……旧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东揪西斗,一天被整数次;有时“疲劳”轰炸,几十个小时不得合眼……
这只是我零零碎碎听人说的一星半点,谁知道他受了几多苦难,咽下几多悲愤呀!然而,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坚毅倔辈,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正气凛然!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其他60名战友的政治生命,为着马列主义真理,为着共产党人的信念而活着!
他不是简单地活着,他还在作殊死的斗争。他在每天看过的报纸上,都要记上所受的批斗和遭到的折磨。他知道,专案组会把这些收集起来,作为对抗 “文化大革命”的证据,但总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那些历史罪人的犯罪铁证!如果说这是他的准确的预见,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还把对他的批斗会,当做一个揭露林彪、“四人帮”可耻阴谋的讲坛。专案组在一份向康生的报告中说:“薄一波仍负阴顽抗,态度极为恶劣”,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显然这使他饱受了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之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真理并非俯拾即是的草芥!他还忍着残酷的折磨给他带来的痛苦,写了一份近 3万言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61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斗争的肯定与赞赏。这就给“四人帮”一伙一记响亮的耳光,揭穿了他们制造这一旷古奇冤的阴谋,并宣告了这一阴谋的彻底破产!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由悲伤而气愤,由气愤而慨叹。什么铮铮铁骨呀,什么忠心赤胆呀,这些赞誉之词在一波面前显得如此平淡无奇,是远远不足以形容一波风骨与肝胆的。
“真没有想到,你坐了国民党的牢,又坐林彪、‘四人帮’的牢。”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吃足了苦,受够了罪了。”
“坐牢嘛,还能舒服得了?”他嘿嘿一笑说,“不过嘛,坐国民党的牢,每天还可以放一次风,他们也允许亲友探监,送点吃的、用的。我们在狱中还办党校,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学习,开展讨论;还进行支部选举,定期改选,过组织生活,作自我批评和帮助同志,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可是,这次坐牢,全都没了。起初还能通过接受批斗了解一些形势,这点‘享受’也不给。几年不让见亲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的身体被他们搞得衰弱不堪,要不是周总理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保护,我早就被那些人迫害死了。”
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哪能说完呢?不过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他虽然比过去苍老多了,但精神很好,调养一段时间,会很快恢复的。只是我不敢提胡明的事,免得几年不见,一见面就要伤心。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即1978年12月16日,薄一波等61位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在随后的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重新肯定了一波对党对人民的贡献,纠正了“四人帮”强加的错误结论。
1979年,一波恢复了工作。
爱的伟人
这年秋天,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一到北京,我们就带着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孩子去看望一波。这时他已搬到万寿园居住了。据说张学良将军曾在这里住过,园子不大,但布局很好,收拾得也很干净,几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坐落在花木浓荫之中,还有一口较大的色塘,水清.见底,游鱼可数,显得恬适而静谧。尚奎和一波是文革后头次见面,激动兴奋,自不必说。一波见了小莉,更是高兴,他把孩子拉到身边,说:这就是小莉呀?你看,十多年不见,长得越发漂亮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该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现在小七已经结婚,你就做我的女儿吧!”说得悲枪凄凉,我心都酸了。
小莉看在眼里,赶紧调调情绪,她对一波说:“伯伯,我以后就是你的小女儿了。”
大家这才开心地笑了。
可是我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胡明不在了,少了大半热闹。一波的孤寂,又显而易见的;我也觉得知音己逝,落寞空虚,不是滋味。当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抑制心底的悲伤,以免引起一波对明姐的思念。
我们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天,才乘车离去。当我回头看到形影单只的一波为我们挥手送行时,鼻子又是一酸,在他旁边,原是有个喜笑颜开的胡明的,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小莉,你看薄伯伯多么寂寞呀!”我对女儿说,“我和你爸爸难得上一次北京,你在这里工作,要常常去看看他。”
小莉很喜欢薄伯伯的热情幽默,也知道胡明阿姨生前对她的疼爱,所以常去看望一波,为他驱赶一些寂寞。有一回,小莉被一个新来的警卫人员挡在门外,说:“首长不在家。”其实他就在隔壁看电影。小莉留下张条子,转身走了。一波回来看了那条子,把警卫员好训了一顿;“你知道我和杨家的友谊吗?你为什么不把她送过来看电影?她就是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吗}?”下回小莉再去时,警卫赶快过来道歉,说:“上次首长对我发一顿脾气。很对不起,小公主!”小莉说:“不认识嘛,哪能怪你呢?我要事先打个电话来就好了。”
当然,任何其他安慰都无法阻止一波对胡明的思念。尽管他口里不说什么,但胡明死得那么蹊跷,他心里怎能安宁呢?而且孩子们也大了,他们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弄清母亲的死因。上级机关也多次派人调查,最后只能确认胡明是被害而死,但谁害的?怎么害的?却没有具体结果。再查也查不出个明白来,薄家只好同意单位意见,给胡明平反昭雪,了却这桩惨案。
1979年4月,我们接到为胡明开追悼会的通知,本来尚奎也要去京的,正赶上省委召开会议,他无法离开,只好由我全权代表了。于是我乘飞机直达北京。薄家的六.儿贝贝前来机场接我。在机场到市内的汽车上,我问贝贝,你妈妈究竟怎么去世的,现在查清楚了吗?贝贝告诉我,那年一波在广州被抓走之后,胡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幸免,迟早是要被揪的,不但思想上有了准备,而且还将换洗衣服、盆洗用具和常用药物放进一个提包里,以便随时提着进“牛棚”。没过几天,几个貌似谦恭客气的干部模样的人,开了一部面包车,到广州小岛招待所来找胡明,说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请她去一趟,胡明信以为真,那个准备好的提包都没有带,便随来人走了。孩子们还以为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没有在意。谁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胡明一上汽车,便被那几个人拉往火车站,架上从广州直开北京的火车,还没到株州,她就已奄奄一息。造反派在株州车站把胡明拖下车,说是送去抢救,可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就含恨而逝了。医院对胡明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说是发现了她食道里有几片安眠药。于是造反派们便给她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而草草火葬。真是荒唐透顶!胡明何罪之有?干吗要自杀?她是被骗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哪来的安眠药?这显然是被谋害而死的,为什么不查出凶手?如此草营人命,着实骇人听闻,国何以堪,民何以堪啊!
他还谈到自己和兄弟姐姐们这些年的悲惨遭遇,桩桩伤心事,催人阵阵泪下。
4月25日上午开追悼会的那天,我和林佳媚、余叔坐一辆车同去八宝山公墓。胡明的灵堂布置得很好,四面摆满了花圈。正面墙上,挂着为胡明平反昭雪暨追悼大会的横幅;横幅之下、墙的正中,是胡明的大幅遗照。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和他们的夫人,有胡明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挤了满满一礼堂;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可是我顾不上和他们打招呼了,因为我一看到明姐的照片,就想到她活着时坦率、乐观,笑口常开的样子,想到我们在一起亲亲热热,窃窃私语的情景,我的眼泪便从心头一涌而出。待主持者宣布开会、哀乐声起,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不知道谁在致悼词,更不知道悼词里说些什么,只觉得明姐从那照片里走出来,走到我前,流着泪说:“永别了,静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于是我痛哭失声。一条手帕被泪水湿透了,拧干了再擦,又湿透了。旁边有人塞给我一条手帕,我也没抬头看看是谁,接过来便用,一会儿又能拧出泪水来。•十多年了,积在心的对明姐的情感、哀伤,在一波和他们的孩子面前强压下来的悲痛与追念,今日全化作泪水,一下迸发而出。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竟有这么多眼泪::
追悼会开完了,我仍止不住哭泣。抬头看看给我手帕的人,原来是王光美同志。
我疲乏极了,虚弱极了,不得不在北京休息几天.
这日上午,一位我和胡明的共同朋友来看我,我们从胡明谈到一波,发了不少感慨。
“哎,水静,我有个想法。”她说。“胡明去世十几年了,你人问问一波,看他要不要找个老伴。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们帮他物色一个怎么样?”
“我这几天还是总想着胡明,感情还没转过来,我不忍心、’我说,“恐怕一波也还处在对逝者的思念中没有清醒.现在去问他这些事,他会不高兴的。”
她想了想,也就罢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同尚奎因事去京时,那位朋友又旧事重提。我了解一波对胡姐的感情,了解他情操的高尚和爱情的专一,估计他是不会再娶的。不过, “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有个老伴照顾生活的确是一种需要。因为孩子们再好,也不会像老伴那么体贴入微,他们不懂老年人的心理.与身体的变化;何况他们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有一堆家务事,工作又忙,能有多少时间花在老人身上?所以,许多丧偶的老人重找老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支持的。
于是,有一次与一波闲谈时,我便趁机说:“有人要我来打听一下,问你需不需要再找个老伴……”
不等我说完,他就摇摇头。“我出来工作之后,别人介绍的也有,毛遂自荐的也有,信件和照片都一大堆哩,我全都拒绝了。”他很坦诚地说,“这倒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挑剔。不是的:,我只是想,老来找伴,为的是彼此照顾,相濡以沫,这首先就需要感情。我看找上门来的,谁对我有感情呢?看上的是我的头衔,而不是薄一波。再说,任怎么找,也找不到胡明呀!”
我又追问一句:“那你真的不再结婚了?”
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地回答说:“当然!”
我敬重他的纯正的、始终不渝的情感,钦佩他的明智的选择。他家有7个孩子,男孩子都结了婚,有妻子儿女,这么大一个家,除了明姐,谁能操持?我看到过一些重新组合的家,因为子女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闹得矛盾重重、鸡犬不宁,老人不但不能安享晚年,反而整日陷于烦恼之中,结果懊悔不已。所以我点点头说:“那也好。”
他轻轻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
此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这件事。我知道,他的不再续弦,主要是出于对明姐不变的爱。有一次,他出访欧美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尚奎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他道乏,并询问他的身体如何。
他回答说:“一切都好,就是身边少了一个胡明……”
身边少了一个胡明,那是因为他心里永远藏着一个胡明。一个永远不亵读这种感情、永远珍重这种感情的人,无疑是个高尚的人。
我更加敬重一波了,我也更为明姐而庆幸,有了这样一位丈夫,有了这么一份情感,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可以含笑暝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