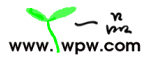我在朝鲜战场的敌工生涯/王乾德
档案春秋 发表于 2009/10/06 06:04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1950年10月,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我在当时培养新中国外交干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和许多同学们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当时,我们都听说,朝鲜前线急需外文干部,审讯俘虏没有懂外语的人参与;缴获的文件没人翻译,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可能就这样无形中流失。听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些懂外文的知识青年更应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在北京,我们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欢迎。肖华副主任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作了形势报告。随后,我们被送往沈阳,在那里经过简单的教育培训和发放冬装后,很快就跟随部队从辑安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争。想不到,在朝鲜一干就是8年,从1950年11月一直到1958年8月志愿军最后撤军才回到祖国。
难忘的战地采访
我参加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所属的20军,二次战役期间,我们军和兄弟部队一起,于1950年11月27日夜间秘密完成了对东线长津湖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将美军陆战1师、陆军第1师、陆军第7师、第3师所辖4个团、3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共1万多人团团围住。仗打得十分艰苦,但我们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经过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迫使美军全线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
初战告捷,我和部队的同志们一样,怀着激奋的心情,在胜利的喜悦中总结工作。20军有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杨根思,带领全连顽强战斗到只剩他一人,最后他抱着炸药包冲人敌群,与敌同归于尽。当时,部队涌现出的英雄事迹实在是数不胜数,首长让我立即去一线部队的最前沿进行战地采访。
在硝烟未散的长津湖畔,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娃娃兵”。我还没有开口,他已经两眼泪汪汪了。我纳闷,打了胜仗,怎么还流泪呢?这位小战士哽咽着对我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战役打响后,这位小战士所在的小分队,负责监视和拦截敌人溃逃时的散兵。冰天雪地里,号称建军以来没有败绩的美军陆战一师,被我埋伏部队打得丟盔弃甲,四处逃窜。我所采访的这位小同志所在的小分队,因为伏击时间较长,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因匆匆过江连冬装都没有来得及换上的夹衣,戴的是大盖帽,因为天太冷,只有毛巾包着脑袋和双耳,脚上穿的也还是单鞋。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埋伏时间长了,腿脚冻僵了,手冻得麻木了。在敌人溃退时,小分队的战士们嘴里在高喊“冲啊!冲啊!”可是,腿冻得陷在雪地里拔不动,枪栓也拉不动了。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跑了,真是欲哭无泪。这位小同志对我说:“首长,你说我能不伤心吗?”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安慰他,只好强忍着伤感,违心地说:“小同志,你还会有机会打美国鬼子的!”事实上,我知道,其实这位小同志也知道,为了保全生命,冻坏的腿弄不好要截肢,小小年纪很可能成为终身残废,他怎么会不流泪呢?
临别时,这位小战士交给我一样东西,那是一枚子弹壳。那是每个上前线冲锋陷阵的士兵和军官都必须有的“身份证”。弹壳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记载了这位小战士的姓名、部队番号和本人籍贯、家庭地址,子弹壳口用蜡烛油密封。他说:“首长,朝鲜战争胜利了,不要忘记我这个小战士。”这时,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回到部队,我把采访情况连同小战士交给我的子弹壳,都上交给部队政治部。当时,我真应该要求领导把这枚子弹壳启封,拿出里面装的小纸条,让我再仔细核对一下这位小战士的情况。可惜,当时我疏忽了。所以,这既是一次难忘的战地采访,也是一生中难忘的遗憾。
战地审讯俘虏
战斗胜利,我所在的部队俘获了大批俘虏。因为部队要继续投入战斗,所以战俘必须立即送往后方俘虏收容站。在前线,只能对战俘进行简单的集体讲话,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然后登记造册,送往后方。
这时政治部主任让我找一名下级军官,他要亲自审讯,我就挑选了一名尉级军官,让警卫员带到首长那里,他审讯,我作翻译。坐下来以后,我让俘虏把头颈上的“狗牌” (DOG TAG)取下来,那上面有他的姓名、军号、籍贯等等。这个“狗牌”的作用,是当他战死了,收尸的人就会把他颈上挂的“狗牌”取下来,塞在他的牙缝里,这样不至于成为“失踪”而无法查找的“异乡鬼”。
审讯开始,首长先对战俘作一般的提问。这些他都比较听话,也顺顺当当地作了回答。可是,再深一层的提问,他就不作声了。他虽然当了战俘,好像还傲气犹在,内心的不服气也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但他又很心虚,怕我们会处置他。首长猜透了他的心思,耐心地向他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解除他的顾虑。开始他还是那么傲慢地说:“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俘只回答我上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其他可一概不作回答!”首长说:“你当了俘虏还那么傲气。你们是战败者。”后来,几经首长开导,他说出了心里话:“我们是被你们打败了。但我们不服输。你们有本事,就在大白天,摆开阵势,大战一场,看谁输谁赢,何必打埋伏仗,打夜仗?”这一下,倒把首长说得笑起来了。他笑这个年轻的美国大兵,怎么会懂得我军的战略战术,又哪里懂得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随后,这个战俘的话匣子好像打开了,表情也放松地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战的。长官们告诉我们远东这里有日本的姑娘和大丘(南朝鲜地名)的苹果,打败了敌人,最迟在‘感恩节’前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听了这些,首长沉思了一会说:“你们是被骗来当炮灰的,为了和平,你们为什么从太平洋东岸跑到太平洋西岸来,侵略别人,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呢?”战俘无言以对。首长又讲了一些话,就让他走了。
战俘走后,首长问我:“小王,今天的审讯,你有何感觉?”想不到首长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首长说:“敌军的基层士兵是被欺骗来当炮灰的雇佣军,他们明白了事实的真相,那么士气是不能维持多久的,这就是他们的劣势。我知道从敌军基层军官身上是了解不到军事情报方面的‘油水’的。今天的审问倒是为我们开展对敌军‘心理战’提供了一些思路。你把战俘的心理特点、心理状况、敌军欺骗宣传的内容和实质,写一份材料,我看了以后报9兵团政治部。”首长还语重心长地说:“小王,看来你们做敌军工作的,尤其需要学点国际公约和条约方面的知识,了解一些美国国情。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这一次参与审讯俘虏,我从首长那里得到不少启发,也受到了教育。通过审讯战俘,我透视了美军思想上的“软肋”。在往后的战役里,经过我训话和填写战俘登记表的不下200多名美军和杂牌军的战俘,凡是碰到重点对象,我就格外留意,仔细审问,了解军情,了解他们的心理和士气,为上级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前线战地坑道里的对敌广播站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以后,敌我双方基本上是处于战略对峙的阶段,我军采取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种态势,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其间,1952年5月和7月曾经有过我军的较大规模的夏季反击战役。这对我军来说,既是战事,更是政治斗争。经过这最后的较量,“联合国军”才不得不在朗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承认自己的失败。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进行火线瓦解敌军的通知精神,我军在前沿阵地的坑道里建立了对敌广播站。讲到坑道,那是既坚又固、深邃幽长,有好几个出入口,里面还有什么上海路、南京路、天津路、四川路等等,在岔道口还设置了路标,不然的话,进去了不记路名,不看路标,就会迷失方向,走错了出入口,那可是事关军事机密和部队的安危。坑道的最大功能是:“你打我,我让你打不着;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据不完全统计:我军共构筑坑道1250公里;战壕、交通壕6240公里。这种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有生活设施支撑点的坚固阵地体系的形成,为我军实施阵地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就是在这样铜墙铁壁般的前沿坑道里,我一线部队的敌工部门办起了瓦解敌军的阵地广播站。当时,敌我双方对峙,有时敌我双方各占一个山头;有时敌我双方近在咫尺,甚至一条战壕连接敌我双方,中间只用铁丝网相隔,在夜深枪声炮声寂静时,从敌方碉堡里传出来的讲话声和咳嗽声都可以清楚听到。这是开展对敌广播的有利条件和实施“心理战”的有利条件。
阵地对敌广播站一般由四到五人组成。其中有一到二名英语、朝语广播员,我当时就担任英语广播员。此外,有一名机务员、一名电话员、一名手摇发电机的摇机员。设备就是一部扩音机、一部手摇发电机、一框电话线、几只广播喇叭。
对敌广播站设在坑道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线部队也很关心我们,但工作条件仍然非常艰苦,只有几平方公尺的地盘,头顶上不停地滴水,后来部队战士帮我们用几块大雨布,撑起天棚挡住滴水。广播时照明用蜡烛也是特殊照顾的,平时坑道里用的都是油灯,广播时亮度不够,看不清稿件会出差错,只有蜡烛灯光才亮一点。
至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凡是看过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都可以回忆起来。每次上阵地到对敌广播站却是比较危险的。到前沿阵地去,虽然走的是战壕,但狡猾的敌人,就在我们上阵地必经的战壕处,用炮弹轰开一个大缺口,夜里用探照灯把这一个缺口照得如同白昼,敌人只要听到动静,就是一梭子机枪子弹射过来。记得我第一次上前沿阵地广播站,是由前线部队的战士护送我上去的。当要经过这段有缺口的战壕前,这位战士先用一根粗树枝在缺口处晃上几下,造成一个阴影,发出一些响声。敌军以为是我们在通过这段战壕,于是就射过来一梭子子弹。这位战士和我都伏在地上未动,等了一会战士先低身跑了过去,再等一会,根据战士的手势,我也快步跑了过去,等我们两人跑过去后,敌军又一连打了两梭子机枪子弹。好在我们已经通过了危险地带。后来我们从俘虏口中得知,一些在碉堡里的敌军,将绳子绑在机枪枪栓上,有时连观察瞭望都懒得做,每隔几分钟,一拉绳子打出一梭子子弹,以此应付差使,当然,对第一次上阵地广播站的我来说,通过危险地带,内心自然比较紧张。
阵地广播站里最辛苦、最危险的要数负责接线和安装喇叭任务的电话员了。我们的广播线埋得再隐蔽,广播喇叭伪装得再好,敌军只要一听到我们的广播声,机枪子弹就对着放声的喇叭打来,有时还向我阵地射来几发炮弹。不是把喇叭打哑了,就是把广播线炸断了。这时电话员就得跑出坑道,冒着敌军的炮火去接线或去换喇叭。一次,我正在广播,突然喇叭哑了,电话员老吴跑出坑道,一查是广播线被打断了,老吴立即动手去接线。这时,一发炮弹射来,炮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还没有等抬下阵地,他就牺牲了!大家悲痛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我们阵地坑道对敌广播站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军。有时也肩负着对内鼓舞士气、活跃文化生活的任务,大凡我前线小股分队向敌阵地发动攻击时,我们广播站就担当起“冲锋号”的角色。在部队出发前,为他们播放雄壮的进行曲;在部队迈出坑道,冲向敌阵地时就播放《志愿军战歌》;在部队胜利归来时,为战士们播放欢快的乐曲。前沿阵地坑道的战士们把我们当作他们战斗集体的成员,大家融洽相处,互相帮助,白天广播站暂停工作时,我们就教部队的战士唱歌写字,为他们代写家信,战士们可高兴了。这些也是在阵地广播站里难以忘怀的往事。
停火72小时与美军“联谊”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在停战停火72小时以后,双方要脱离接触,撤出非军事区。因此,这72小时,是宝贵的与敌接触开展工作的好时机。
停战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前沿阵地,一下子一片死寂,当时还真有点不习惯。为庆祝胜利,一夜之间,在我前沿阵地上搭起了欢庆胜利的高高的彩牌楼,也不知朝鲜老百姓,怎能如此神速。彩牌楼上插起了彩旗,扎满了松枝和“金达莱”花。这反映了朝鲜人民胜利的喜悦和骄傲!
停火72小时,双方要撤离阵地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这时我们抓紧时间,主动向我阵地对面掩体里的敌军喊话让他们出来晒晒太阳。并说:“你们就要走了,我们交个朋友好吗?”听到我们的喊话,敌军人员陆续从碉堡里走了出来。但是,要他们先走下山头,来到较平坦的中间地带,看来他们心存的疑虑不少。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几名懂外文的同志争取主动走下山头,来到中间地带。见此,美军的士兵也一个一个从山头上走了下来。几天前,还是兵刃相见的敌对双方碰到一起,相互间戒心难免。我们的警惕未因停战而稍松懈,仔细观察他们是否带有武器,在确认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主动伸出手去与他们握手,想不到那个把手伸过来和我握手的美军下士,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他的手又大,我都感到被他握得有些酸疼了。我们相互寒暄几句,说了一些美好祝愿的话。下来的都是士兵,他们的长官在上面监视着他们。握手、聊天以后,相互交换纪念品,我们有的送他们一瓶酒、有的送他们一包中华烟。我不会抽烟喝酒,就拿出一张我特别喜爱的《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照片。这个美军下士看着照片上抱着和平鸽的两个孩子,高兴得很,情不自禁地拿起照片亲吻了一下。他也想送我一件纪念品,可摸遍了口袋,找不到一件合适的东西,最后他在腰包里,找到了一张塑封的照片,背面是一络金发。他告诉我,照片上的女子是他的妻子;金发是他和妻子离别时剪下来的,塑封在一起,好让远离家人的他能时常看看照片,聊以自我安慰。他说:“现在停战了,我可以回家和她团聚了,也不用再把照片带在身边了,就给你留个纪念吧!”他的思乡思亲之情,溢于言表。
72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双方都撤离了阵地,脱离了接触。我们前沿阵地的部队,仍然在非军事区外面的阵地上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同时,还肩负着在非军事的分界线我方一侧的安全通道里执行武装巡逻的任务。瓦解敌军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
军事分界线上的对敌心理战
以和敌人“交朋友”的形式,进行“心理战”,瓦解敌军,这是我军对敌政治工作中的一个老传统。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在军事分界线各自的一侧,辟出一条“安全通道”,即双方在各自一侧的宽2米的军事分界线上进行扫雷及排除其他障碍,形成一个“安全通道”,双方各派出3到5人的巡逻小组,在各自的安全通道里巡逻,任何一方都不得超越军事分界线。在巡逻中我们臂上戴的是标有“民警”两字的红袖布;敌方戴的是标有“MP”(宪兵、武装警察)字样的兰黑色袖布。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允许带一支步枪和配戴一支手枪;敌军的武器装备比较先进,他们的步枪是半自动的,可以连发,所以只允许他们带一支步枪巡逻。我们就利用这个巡逻的机会,以“交朋友”的方式,对敌军开展“心理战”,瓦解敌军。因此,在每个巡逻小组里,除前线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以外,根据敌方巡逻小组人员的各异,配备懂英文或朝鲜文的敌工干部。当时,我就作为懂英文的敌工干部参加巡逻小组。
在巡逻中,双方都是荷枪实弹,停战不久,对方敌意甚浓,警惕性和敌对情绪,溢于言表。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虽然警惕性一点也不放松,但表面上却是以“友好”的姿态出现。我们工作决不能“操之过急”。开始,我们在巡逻中相遇,有时只是一笑擦肩而过;最多是一声“礼貌”的问候或讲天气等等的无主题的交谈。数次接触以后,话开始多起来了。当然,话多数是接着他们的“由头”,我们后说多说。为了延长接触和交谈的时间,巡逻的脚步从开始时,双方匆匆而过,到后来双方心照不宣地放慢巡逻的步伐,谈话的内容也慢慢延伸到对方的家庭、妻子、儿女等家常事,这些事对方一般是愿意涉及的,而且好象也没有多少顾虑或保留。但边走边谈,毕竟时间短暂,巡逻结束时,我们感觉到对方言犹未尽。于是,我们主动提出,可以采取“约会”的形式,到一个军事分界线中间地带合适的地方坐下来交谈。对方欣然同意。为了表示我们的“友谊”和“诚意”,我们还带了一些休闲食品、中华牌香烟和一些小礼品。这些都是为了工作需要专门从我国国内采购来的,其中不少还来自上海。然后,双方席地而坐,话题从家庭生活切入,谈到他们的入朝作战的非正义和他们受骗上当当炮灰的实情。开始他们听的多,后来也和我们争辩几句我们倒是喜欢他们的争辩,这表明他们的心中已把我们当成“朋友”了。“约会”的次数多了,熟悉了,我们带的消费品和纪念品也多一些了,而对方却永远是两手空空,对此他们有时自感腼腆。有时,我赠送给他们纪念品,他们搜遍衣裤口袋,找不出一件可以交换的纪念品。一次一个美军黑人士兵竟拿出一把军用卡车的钥匙给我作纪念,我没有收。车钥匙没有了,回去怎么交待,怎么开车呢?一次一个美军士兵,掏出一张照片给我,这是他的“全家福”,并给我一一作介绍;谈到他儿子时,他面带骄傲地说:“我儿子足球踢得好,将来一定是个好球员。你留着照片,以后会在赛场上见到他的!”我欣然接受。在多次约会以后,对方对我们树立了信任感和好感。有时,预定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们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从阵地上下山去应约,他们会在约会的地点久等,而且举起双手给我们打招呼,要我们下去。遇到他们的部队换防,他们会预先告知;有时他们巡逻小组里来了陌生人,可能是长官,也可能是特务,他们会对我们发出暗示,让我们提高警惕。
在军事分界线上的对敌“心理战”中,一定不能轻敌麻痹,放松一丝警惕。这方面是有血的教训的。一次我们一个巡逻小组,与南朝鲜伪军的巡逻小组,事先约定了“约会”,到时我们巡逻小组带着米酒和下酒菜下去了。刚坐下,还没开言饮酒,一个伪军特务就拔枪向我们巡逻小组里的朝鲜文敌工干部迎头一枪。这位干部当场牺牲。
对敌“心理战”中,我们不求“立竿见影”,也不搞“旁敲侧击”,示意他们与长官作对,更不会启发他们“弃暗投明”。这一是不必要,二是办不到。只要在巡逻中,通过我们的交谈约会,能让他们得到启发,能够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军事分界线上的对敌“心理战”,是我在朝鲜的8年时间里,从事瓦解敌军工作的最后一站。在我部队撤离前沿阵地,朝鲜人民军来接防时,我们把对敌“心理战”的工作向朝鲜人民军的领导机关和接防部队作了移交。
1958年夏秋之际,在朝鲜8年的我和志愿军大部队的同志们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第二故乡——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片热土上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20岁到28岁)献给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