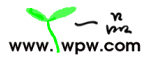清未新军的国家失控
苏全有 发表于 2009/09/28 22:37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苏全有
清王朝的灭亡乃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对清末新军的失控是重中之重。目前学界对清末新军的研究,多取自下而上视角,自上而下探究新军失控的原因者乏见,且一概归咎于积重难返,不可救药。这样的研究既显单一、片面,又似不负责任,缺乏价值与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清末新军为考察中心,针对清末中央政府军队控制失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一、革命宣传的公开性特征
清政府编练新军,基本动力来自于控制军队,而结果却很失败,这可从清末革命宣传的公开性特征看出。在湖北,革命党人设立秘密印刷所翻印革命书籍,因为通俗易懂而且可以歌唱,在新军中影响很大,“官长目兵,公余之暇莫不奢谈革命,互相砥励,其以《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孔孟心肝》以及《民报》诸刊物作为诱致之宣传品”。革命派还掌握《商务报》、《大江报》等报纸,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以至声誉日起,销路日增。再加上湖北新军营中设有专门的“阅报室”,命党人又在营内大量散发报纸,如《大江报》就在新军各标营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平日免费赠送各营队“义务报”一份,所以报纸能够深入军营,直接到达新军士兵手中。结果,《大江报》“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其在军中之“权威殆无出其右者”,而受《汉口商务报》之熏陶者,“无不益自淬励”。
在南京第九镇,据何遂回忆:“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
在广西,革命党人“革命宣传是多样化的,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常在课堂上阐说种族大义”。何曾经慷慨激昂地对大家演说,声称 “我们要让满州人统治下去,不久就当了亡国奴”,宣传“孙先生的党徒遍于天下,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起来振臂一呼,就会天下响应”。据杜誉钦回忆,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里,“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很注意。在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时,常以外国的军队为假想敌;在精神讲话中常讲到外交失败,旧军腐败无能,对外作战失败,国家有危亡之祸,勉励学生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等。当时进步的报刊,如《南风报》、《民报》、《梧州新报》等,在自修时间都有得看。”
在云南讲武堂,“当时的新书报,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云南》,在学校中争相传阅……”。[93(Pt6)据朱德回忆,当时云南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宣传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讨论和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李根源则利用他充任总办的便利条件,“常不避危险,灌输革命思想于诸生”。如1910年正月,李根源同教官李烈钧、顾品珍率学生到黑龙潭演习,之后,便带领他们参拜因反对清军入关而全家沉黑龙潭自尽的薛尔望的坟墓。回到讲武堂,即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参拜薛尔望先生墓呢?可惜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然,我们中国就不会像这样。”该学堂教官,也“经常利用精神讲话,在上课时间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们以举例、暗示、影射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反清革命的思想感情。学生在校,受革命思想薰陶,思想趋向革命,毕业后,他们多数充任新军下级军官,又“向士兵进行宣传革命思想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给辛亥重九光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广东革命党人也“经常利用星期假日,邀约官兵去白云山附近地方集会,演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山东黄海之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王入粤等惨痛史实”,其目的都在于揭发清廷腐败,辱师丧国,必须推倒。这样的演讲,效果极佳,“常常感动得新军们抱头痛哭”。在东北,1909年在驻新民府的北洋新军第一混成协中成立了一个革命活动的组织,主要人物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冯玉祥回忆说:“我们每天聚到一起,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等具体问题,或是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在陕西,培养下级军官的速成学堂的学生,还组织了一个军人革命团体——“同袍社”,进行革命活动。
如此公开的内铄式革命宣传,表明清政府对新军的失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结果是,“陆军新学生皆饱吸新空气,多加入同盟会。”新军中许多军官曾留学国外,“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即未加入同盟会者,亦均同情革命”。新军“为革命潮流所激荡,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虽因时代关系,对社会民众福利之观念未能深厚正确,而倾向共和之精神,则确为当时新军中级官以下所一贯同具”。到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一旦革命爆发,他们有可能“全都投向革命”。正如孙中山说道:“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业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人;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
清政府对新军失控固然有江河日下的客观外在原因,可如此公开化的宣传革命之现状,其自身的举措方面一定有失当之处,当无疑问。
二、清政府的失误
对于革命派宣传的防范,应该说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清末新政确定的教育宗旨即“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着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军校的课程设置也注意强调《四书》、《五经》等封建旧学,“以固中学之根柢,端学生之趋向”。些学校还明文规定,逢皇太后、皇帝及孔子生日,全校师生须集合礼堂行三跪九叩礼,烟台海军学堂以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命名该校的八个班级。对于出洋学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一129—五颁发的上谕要求“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强求”。清政府还颁布《训练制略》强调, “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精其技艺,增其材力。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立志报国。”
防范之外,清政府对编练新军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也并非熟视无睹。1906年,端方密奏称,“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自安徽新军炮队队官熊成基及巡警道徐锡麟等案发之后,清廷对于军警、学生,戒备加严,尤以军中为甚。”1910年1月广州新军起义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奏折中称:“综此次各兵所供投身会党,冀图乘间起事,并夺械戕官,昌言革命,几无异词。尤以黄洪昆一犯所供为最详尽,且亲笔书写,神色不变。并据供称新军为革命党出力,非为国家,其散布票纸有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四言句,且伪立天运年号。该党军制亦有统领标统各名目;其运动所至,以各省军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练熟。……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又煽乱于后,且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其病根误听自由独立之学说,而外来之诱胁遂以乘之。腹心可忧,燎原亦可虑,应请传旨练兵各省分,严加选练,力杜波邪,为思患预防之计。”闭(P214-215)清廷“上谕”也指出:“近来人心浮动,各处会党丑类繁多,往往混入军营,暗中勾引,借端煽惑,广东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预防,早图挽救。”1911年御史温肃奏道:“国家岁糜巨饷以养新军,原欲收干城腹心之寄。乃自逆党肇乱以来,军界中多为其党羽……今不速为整顿,岂惟糜饷费时而已。养虎自卫,臣窃为朝廷痛之。”
既有防范,又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还会出现革命派大张旗鼓的宣传场景呢?原因有四。
第一,中央政府的无能。清末中央政府作为新军建设的领导者,革新机制很不健全,缺乏远见与决心,整体素质低下,根本就不具备成功领导者应具有的能力。慈禧关注的是个人权利,之后的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清廷统治者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
第二,就心态而言,清政府情绪急躁。清末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年,理性为激情所取代,成为特殊的、非理性的时代。过去学界往往强调民众、革命派的非理性,其实,清政府及其所领导的现代化事业也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托克维尔曾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清政府对于新军建设的危险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裁汰旧军迅速而坚决,并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普设新式学堂,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以填补传统教育的空白。对此,L_T.怀特分析道:“终止科举制度的行为,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亨廷顿也指出:“成功地领导改革的政府,不仅能够创制政策,由国家来采取行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力量。”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新思想、新的价值观,进入新军后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而非拥护者,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正如费正清所指出:“为革命铺平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中国人的生活中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与之不相容的清王朝竭力想控制变革的方向,但它无法避免反清势力和离心势力的滋长,而正是这些势力最终摧毁了它的统治。”
有论者认为,清廷“只有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第三,对清末新军的控制较为宽松。以湖北新军为例,该军就处于一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境地。湖北地方当局虽然也注意防范党人潜入新军,但为了不引起朝廷对湖北事务的过多干预和指责,它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不予深究的态度,一般将领头者遣离或开除了事。如当局在侦知花园山聚会后,将其骨干或派赴西洋,或遣往东洋,或调入北京,使之无形解散。破获振武学社后,也仅把潘康时等主要人物开除军籍。广东也是如此。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督练公所拟将原来新军遣送回籍,结果是到了第二年秋季广东第二次招兵,新军又完全改换姓名,应募入伍,重新做革命的种子,终于在武昌起义胜利来临之日,在广东起义响应。
当然,也有控制相对严密的地区,如四川新军,饶国梁曾充任第六十五标见习军官,可是由于防范严密,饶的革命活动受到多方掣肘,最后被迫离川赴滇。我们从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新军表现,亦可洞悉一二。只是这样的地方非常之少。
第四,相对弱化了旗兵建设。驻防八旗新军,大多由原来的营队改造而成,甚至只变更名称,许多营队缺额严重,装备和训练仍很落后,素质也较差。如驻防广州的新军素质很差,战斗技术很拙劣,士气也很低落。军事面貌也未完全改观,即使是号称各军之冠的禁卫军,也“真棘门灞上儿戏事耳……其操演亦用新法,然不脱梨园武行习气”。老弱充斥军队的现象仍然存在,如光绪三十四年热河驻防“查有年在六十岁以上前锋、领催、马甲共一百四十四名”。
在清末新军建设中,应该说中央政府对旗兵还是比较重视的。光绪三十年练兵处奏订《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按其规定,每年定额100人,而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等13处驻防和京旗定额就达到了19人,占总数的19%。如果再加上吉林、黑龙江、奉天等省的旗人名额,人数肯定还会增多。据统计,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派出的4期旅日陆军留学生中,至少有90人是旗人。他们毕业回国后,或入学堂、新军任职,或入政府谋官。1906年设立的陆军贵胄学堂,要求学员来自皇室,以及总督、巡抚、各部尚书和侍郎、八旗驻防将军等门庭显耀之地,醇亲王、贝勒载涛和贝勒载洵常去贵胄学堂旁听。只是,上述措施未能满足清末中央政府控制新军的需要。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学界有人以环境恶劣为由在宏观上否定清廷改革成功的可能性,认为清朝统治者终是处于“欲防无计”、“欲罢不能”的困境中。笔者认为此论不足取。不错,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清廷。可这不能成为清政府不思进取的理由,相反,清政府更应针对时势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化被动为主动,从而使局面导向可控范围,进行有序改革,巩固统治。以环境恶劣为借口而置清末新军控制失败于必然境地,这既无学术意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末环境险恶主要是外患日深,这当然是个挑战,可也是机遇。若能借助外患凝结人心,使中外矛盾取代满汉矛盾升格为首要民族矛盾,那么,清政府的政治资源应有增加之可能,当不是什么奢望!用民族危机化解统治危机,这是点破清末困局的要着。学界习惯于在清廷维护统治与抵御外侮之间建立对立关系,从而使得清王朝必然灭亡这一认识成为终结者。
[参考文献]
[1]辛亥革命资料选辑[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王小娟,湖北新军转向革命诸因素浅析[J],青海师专学报,1990,(4)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M],北平:文华斋刊本,1928
[4]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V)[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M],郭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z],南宁: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
[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闭,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l1
[12]冯玉祥,我的生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阁,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2编“军史”)[蜘,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一)[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16]柴德庚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朱有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l辑上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1]苏贻鸣,晚清军校教育与军事近代化[J],军事历史研究,1994,(3),
[22]清实录·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4]柴德庚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26]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六)[z],北京:中华书局,1963,
[2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2]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M],社会科学论坛,2000,(3),
[33]来新夏,北洋军阀(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3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三)[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36]王在民,广东新军的“庚戌起义”[J],学术研究,1958,(7),
[37]席萍安,试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咖,文史杂志,1997,(6),
[38]于城,广州满汉旗人和八旗军队[J],广东文史资料(第14辑),1964,
[39]夏仁虎,旧京琐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40]李德新,清末新政与八旗社会[D],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D06年硕士毕业论文,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2]刘伟,饶东辉,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3]陈文桂,清末新军向革命转化[J],厦门大学学报,1980,(4)
[44]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5]苏全有,史官参政:恽毓鼎的经济思想探析们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