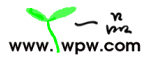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续1)
许允仁 发表于 2008/08/03 14:09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国家认同 公民认同 达赖喇嘛
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上造成的困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模仿前苏联人工划分和制造大量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按族别实施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并将这种族属认同塑造成了民族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从而将其导向了危险的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因为,确实只有变为共和国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完全的自治[12];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生活在美国式的“大熔炉”政策下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就会培养出内涵截然不同的族属认同,前者的族属认同是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的全部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公民身份,而与其族属身份完全无涉;相反,在后者的制度下,他的民族意识被导向了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他的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因此,在他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中,他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某族的一员,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有一种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因为遭到党的一元化统治的遏制,才没有更加激烈地暴发出来,而一旦党治的外部捆绑消失的话,它的离心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党除了用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各个民族之外,也力图在思想上培育各少数民族的个体超越于族属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党国不分的弊端,因而,对国家的认同无法和对党的认同分离开来,而对党的认同又无法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党的领袖的个人认同分离开来。于是,历史变迁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变更,对少数民族成员的稳定的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我们可以以藏人为例,来分析一下,这种变更对藏人的国家认同所造成的严重困扰。在1950年代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将其正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前,西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藏人并没有明晰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太阳,因而,对达赖喇嘛的认同,构成了藏人的全部生活的重心。而在“平叛”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通过在藏人中进行阶级划分和暴力革命,在彻底重构了西藏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藏人的认同方式。
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来的是对“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认同;对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方式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认同;对领导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共产党的认同;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的认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藏人生活重心和精神支柱的藏传佛教被共产主义信仰所替代,达赖喇嘛的位置则被毛泽东所替代。西藏在新的基础上被再次构建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所以,我们看到,上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不是按照现代政治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培养起藏人在法理基础上的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用一种新的对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一种旧式的个人崇拜,假如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是在千百年的传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前者则是通过暴烈的群众运动和精神灌输,在短期内人工构建的。
这种新认同无疑是在血腥的暴力,和精神上的高压下塑成的,然而,就在许多质朴的藏民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新宗教和新偶像,天天对着毛泽东的像顶礼膜拜,亲自动手拆除传统的寺庙,逐渐淡忘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时,执政党本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建立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而且个人崇拜作为灾祸的根源遭到严厉的批判和被摒弃。传统的宗教又被允许在藏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位置。不难想象,这一切在藏人的思想中,导致了多大的混乱。就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描写的那样,由于恐惧和赎罪的需要,那些曾经亲手捣毁寺庙的人,又成为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最卖力的人。而达赖喇嘛在许多藏人的心中又开始恢复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执政党的部分领袖,对在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对藏人造成的诸多伤害充满愧疚和同情,因此,在治藏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怀柔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藏人的许多权利得到恢复,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是,由于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加上长期的高压政策放松之后不可避免的反弹,藏人在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同时,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对党国的认同程度反而不断削弱。
我们看到,胡耀邦虽然怀有对藏人的真诚的善意,但是,其治藏的思路依然没有跳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本族人治本族人”的窠臼,他希望通过让汉人大量退出西藏,和提高藏人在各级干部中的比例的方式来增加藏人对党国的认同,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反思了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与西藏1980年代末的骚乱之间的关系之后,执政党的治藏政策(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调整为: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则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短期地和外在地看,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政治上的强控制,藏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稳定了,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培育藏族公民(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只是暂时被强制性地压下去了。随着经济增长导致的藏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爆发出来。
笔者在《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执政党政治哲学的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一文的结尾,反驳了将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均1000至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一旦超过3000美元,所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会趋缓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预言超过人均 3000美元之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无法塑成的矛盾:即“国家的构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逻辑,能不能得到公民们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制度化的承认”,也就是“执政党的自我认同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趋激烈,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藏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提前爆发出来。无疑,这一矛盾最终只有在执政党通过政治哲学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而作为准备性的工作,下面我们打算对这样的妨碍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四、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以及如何培育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
当我们通过分析,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一制度必然会驱使少数族群的成员,将自己的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从而引发各种无休止的危险的政治冲突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选择这样的制度呢?
有些学者看到,斯大林在1930年代、毛泽东在1950年代都如此热衷于人为地划分和制造民族,就将这种制度的选择首先归因于独裁者的政治虚荣心。确实,当一个人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被人歌颂时,与被称为“五族人民的领袖”相比,“56个民族的共同的领袖”,或者让人觉得民族多得数不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听上去要辉煌壮观得多。而且,由于在党国体制下,不管制造出多少人工的民族来,它们都要服从党的一元化的绝对统治,因此,在党的领袖看来,在这样没有现实的分裂危险的前提下,制造的民族越多,就越能显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3]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国的领袖手中掌控着越是坚固的绝对权力时,就会越是倾向于去制造更多的民族。
但是,党国领袖的政治虚荣心只是这一制度得以生成的表层的原因,当我们看到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都采取这一制度时,就不难发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共产党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哲学:集体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和宪政国家建立在个人主义,即每个公民个体和国家的契约之上不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在某种前现代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看作是建立在56个民族的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所以,在政治上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不同族群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平等。
在单一制国家内部强调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听上去似乎很公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实践结果上看,都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平等这个概念只是对具有人格的个体而言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和可能实现的,而民族或族群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人格,因而就根本无法从法理上去实现所谓的集体之间的平等,这事实上正是哈耶克所一再批评的将集体拟人化的社会主义谬误的又一次典型反映;从实践结果上看,不恰当地强调所谓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后果是,不断地刺激和强化着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意识。一边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另一边是一个几百万、几十万人口的民族,你不管怎样做,后者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前者在政治上相比是弱小的、不平等的。而且,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同民族(假如以民族为单位来衡量的话)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是由于吸取了以往在民族问题上的沉痛教训,在完成宪政化改革后,才在新的宪法中,将以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提法,改成了各族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所以,和我们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集体主义偏见正好相反,事实上,一个国家假如建立在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纷争和动荡之上,相反,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权利契约上,一个共和国才能真正地建基在磐石之上。
仔细分析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所以会根据一个个体的族属身份的不同,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区别对待,又跟其哲学上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倾向密不可分。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先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的,它相信每个个体都天生拥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基本权利,个体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基于某种永恒的先天法理,而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性的处境和身份毫不相关;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哲学则是建立在经验论和唯物论的基础上,建基在先验哲学基础上的普遍人性和基本人权,在其看来纯属一种抽象的虚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只可能来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阶级的或族群(民族)的身份。
所以,在这种政治哲学看来,当一个人纯粹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只有当他作为现实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集体(民族、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时,他才拥有和分享了某种政治权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赖以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东西,和在宪政条件下,公民赖以结合成一个共和国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前者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习俗和文化等经验性的存在,因此,不能分享一个民族的这些基本特质的个体,在一个建立在前宪政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必然遭到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后者则是超越于变化不定的经验因素之上的恒久的权利,只有一个建立在这种超验权利之上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公民,和获得超越于经验变化之上的坚固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人工地制造“民族行政单位”的做法,同时也是哈耶克所批评的用一种僭妄的“构建理性”去设计社会工程的“致命的自负”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当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改变为少数族群的观点提出来后,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反对的理由是,从部落到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一自己设定的单一进化公式出发,他们不理解族群到底算什么东西,在他们看来,用人工的方式去制造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是在按照“历史规律”帮助一个个人类群体在实现自己的进化,相反,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民族变为族群则是一个倒退。
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多民族条件下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又给每个民族以完全的政治上的自决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个矛盾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拥有完全的政治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完全地服从一个维系单一制国家存在的政党的绝对统治,从逻辑上说,要使这两者不矛盾的唯一可能就是,各民族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绝对服从党的统治,而党的统治意志正好和各民族的政治意志完全同一。所以,就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终结果,非但没有给少数民族的公民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反而更增加了精神领域的专制带来的虚伪和矫情。少数民族的公民非但并不拥有更多的政治上的自治权,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治权,只是出于自愿才完全服从党的绝对统治,党的意志总是天然地代表和反映着本民族最真实的政治意愿。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对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大国来说,解决族际矛盾的恰当的方法,不是将这个国家建筑在一种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建筑在个人主义的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因为,一种缺乏明晰的个人权利观念的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必将在这个国家内部制造民族间的分裂,在外部则引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对抗。极权体制下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于制度性地不断塑造和强化着少数族裔公民的高度政治化的族属意识,因此,总是会一方面在客观上不断地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提供着顽强的精神资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另一方面,为了在现实政治中维系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则不断地强化一党专制和极权政治,这一制度所内含着的尖锐矛盾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和社会震荡。
而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每个公民才会在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对等地承认他人的权利,不同族群的个体才可能超越各自不同的族属身份相互间认同对方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同时维系对一个平等保护每个个体权利的法治国家的理性认同。在这样的政治构架下,每个个体在政治层面上拥有完全同质的公民身份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可以真正自由地保持不同族群的特质和多样性。所以说,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以重构,才是最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1990年代采取的经济上优惠,政治上高压的政策暂时压住了这一矛盾,但是,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标志着民族问题再度变得尖锐起来,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怎样理解和界定这一系列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民族事件的本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种肤浅和轻率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完全只是由类似达赖喇嘛这样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挑动起来的,因此,只要通过专政手段消灭这些分裂主义者,或者用消极的方法将其“拖死”,西藏问题(或其他的民族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种目前可能在执政党内占据着主流的看法,事实上正是笨拙的党国体制面对危机时的本能反应。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在面对一系列危机事件的挑战时,一种错误和低级的应对方法就是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偶发事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各自应对,或者通过将其归为敌人的阴谋的方式来逃避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一个成熟的组织遇到危机时,则总是像儒学所说的那样,不是矛头对外,而是反身求诚,总是寻求通过使自身得以改进的方式来化解和应对危机。而越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就越是具有一种由微见著的先知般的洞察力,他总是能从反复出现的危机中,洞察到组织得以构成的最核心的理念中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从而通过推动对组织进行深刻的改革,来使其变得更为合理和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认为,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一系列民族事件,对党国这一组织来说,绝非无关大局的偶发事件,而是其深层矛盾的必然反映,它深深地植根于被称为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之中,植根于党国得以构成的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等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偏颇和缺陷之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危机,存在着二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原有民族政策,一方面在理论上高调宣称,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内实行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是一个族群在政治上获得应有尊严的惟一正确和可能的方式,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党对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精神上的极权统治;另一条道路则是上述的通过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方式,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塑造少数族群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
应该看到,这二条道路,二种不同的民族理论都有着自我实现预言的能力。一旦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得不听任党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思想上实行日益严厉和全面的控制;同样,假如我们坚持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小开始就教育每个个体在政治上将自己的公民身份置于族属认同之上,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保持各个族群各自特质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各个不同族群个体的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公民认同,是一件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主题前一文章
| 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 --- 许允仁 2008/08/03 14:05 (15384 bytes) |